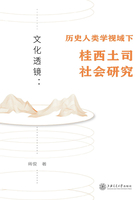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早在民国时期,“边政研究”浪潮下的土司研究在全国蔚为规模,已形成一个大的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群体,烘托起火热的氛围。 但显然桂西土司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则大概是由于当时桂西的边疆危机尚未累积到一定程度,二则可能是原桂西土司辖区人群所表现出来的“异文化”情调不够浓烈。不过,这一时期,一些广西本土学者曾对壮族的历史来源做过广泛的考证与讨论,其中涉及桂西土司的部分内容,主要有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
但显然桂西土司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则大概是由于当时桂西的边疆危机尚未累积到一定程度,二则可能是原桂西土司辖区人群所表现出来的“异文化”情调不够浓烈。不过,这一时期,一些广西本土学者曾对壮族的历史来源做过广泛的考证与讨论,其中涉及桂西土司的部分内容,主要有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 与刘锡蕃(即刘介)的《岭表纪蛮》
与刘锡蕃(即刘介)的《岭表纪蛮》 两著,其所述土司部分都比较简单,但不失开创价值。刘介后来编著《广西特种教育》一书,其中对土司情况有一些介绍。
两著,其所述土司部分都比较简单,但不失开创价值。刘介后来编著《广西特种教育》一书,其中对土司情况有一些介绍。 此外,刘介另有《广西土官故实采访录》一文,对土司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皆有论述,应该算是第一篇全面介绍桂西土司的专文。
此外,刘介另有《广西土官故实采访录》一文,对土司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皆有论述,应该算是第一篇全面介绍桂西土司的专文。
1949年以后,伴随着“民族识别”的开展,桂西土司作为壮族最重要的历史与文化表征之一,是民族识别工作组重点关注对象。在这次调查的最终成果——《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有关土司的内容占了较大篇幅,记录甚详,且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田野素材,是了解桂西土司制度难得的材料。 此外,1961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组织编撰的《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共4册),基本上是一个文献的汇集,搜罗了诸多正史古籍、地方志、碑刻等所载的土司内容,包括“土司制度产生前的广西社会”“广西土司制度的建立和消灭”“土司的辖地和世袭”等八篇,颇有参考价值。
此外,1961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组织编撰的《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共4册),基本上是一个文献的汇集,搜罗了诸多正史古籍、地方志、碑刻等所载的土司内容,包括“土司制度产生前的广西社会”“广西土司制度的建立和消灭”“土司的辖地和世袭”等八篇,颇有参考价值。
不过囿于各种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关于桂西土司制度的专题和系统性研究一直未曾开展,相关论著几乎没有,论文亦屈指可数。刘介在《宋代僮族地区在土官统治下的经济形态》一文认为,宋王朝在壮族地区建立土官制度,是前代“羁縻制度”的延续,其经济形态仍属于奴隶制。 粟冠昌则讨论了桂西土官的族源问题,他通过考证认为,土官绝大多数是本地的壮族人。
粟冠昌则讨论了桂西土官的族源问题,他通过考证认为,土官绝大多数是本地的壮族人。 此后是一段漫长的研究沉寂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桂西土司的研究才又见诸学术刊物,譬如钟诚以《广西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初探》为题探讨了桂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及结果,
此后是一段漫长的研究沉寂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桂西土司的研究才又见诸学术刊物,譬如钟诚以《广西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初探》为题探讨了桂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及结果, 胡起望对《明史·广西土司传》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校勘与考证。
胡起望对《明史·广西土司传》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校勘与考证。 虽然文章的数量有限,但研究思路逐渐在拓宽,其中不乏值得深入探讨价值的观点。台湾地区的学者关注土司制度者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陈耀祖的硕士论文《土司制度之研究》,该文着眼于中国土司制度的宏观分析,其中部分涉及桂西土司的内容,尽管陈文并无丝毫的人类学色彩,但其参考文献中出现了一些人类学书目,颇具特色。
虽然文章的数量有限,但研究思路逐渐在拓宽,其中不乏值得深入探讨价值的观点。台湾地区的学者关注土司制度者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陈耀祖的硕士论文《土司制度之研究》,该文着眼于中国土司制度的宏观分析,其中部分涉及桂西土司的内容,尽管陈文并无丝毫的人类学色彩,但其参考文献中出现了一些人类学书目,颇具特色。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学术热情与日俱增,桂西土司的研究迈上新的起点,自此成果层出不穷,至今仍是学术热点,不断有新作问世。根据不同的主题,可将40年来的研究成果做如下归类:
一、综合性研究
谈琪所著《壮族土司制度》是第一部研究桂西土司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探讨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土司制度、土官族属、姓氏传袭、土司武装与战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社会教育、文艺宗教、改土归流等问题,但所述零散,近乎论文集的模式,未形成理论性的主题。 粟冠昌的《广西土官制度研究》是一部论文集,收录其多年来发表的19篇文章,讨论了诸如土官民族成分、土司统治区的土地问题、改土归流等引人关注的议题,在史料考证上颇见功底,文章的观点则反映出1949年后学术界关注阶级、土地、进步与落后、民族观等问题的意识倾向。
粟冠昌的《广西土官制度研究》是一部论文集,收录其多年来发表的19篇文章,讨论了诸如土官民族成分、土司统治区的土地问题、改土归流等引人关注的议题,在史料考证上颇见功底,文章的观点则反映出1949年后学术界关注阶级、土地、进步与落后、民族观等问题的意识倾向。
21世纪后,综合性研究明显增多。黄家信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一书,尽管属于历史学著作,但采用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搜集到一些口述、碑刻资料,其中第七章论述了文化视野下的“岑大将军”信仰,有一定新意。 蓝武的《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围绕广西土司制度由产生到确立、由鼎盛走向衰落这样一条主线展开论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扎实的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
蓝武的《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围绕广西土司制度由产生到确立、由鼎盛走向衰落这样一条主线展开论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扎实的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 韦顺莉的《清末民初壮族土司社会研究:以广西大新县境为例》通过对隐含于民间的地方文献的爬梳,探讨了土司制度变迁下壮族乡土社会的内在秩序及其转型,是较为有特色的个案研究。
韦顺莉的《清末民初壮族土司社会研究:以广西大新县境为例》通过对隐含于民间的地方文献的爬梳,探讨了土司制度变迁下壮族乡土社会的内在秩序及其转型,是较为有特色的个案研究。 玉时阶等人合著的《南丹土司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南丹从宋代开宝七年(974年)设土州,到1918年改土归流后设置南丹县期间,该地的沿革与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社会风俗等,对了解桂西土司制度有一定价值。
玉时阶等人合著的《南丹土司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南丹从宋代开宝七年(974年)设土州,到1918年改土归流后设置南丹县期间,该地的沿革与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社会风俗等,对了解桂西土司制度有一定价值。 《白山司志》是保留较为完整的一部土司专志,也是研究桂西土司制度的重要史籍材料,蓝武等对该志做了认真点校与研究。
《白山司志》是保留较为完整的一部土司专志,也是研究桂西土司制度的重要史籍材料,蓝武等对该志做了认真点校与研究。 此外,一些关于壮族、广西以及土司制度等通识性著作也不时辟有桂西土司的专论,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
此外,一些关于壮族、广西以及土司制度等通识性著作也不时辟有桂西土司的专论,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
二、专题研究
随着桂西土司研究的不断拓展,其领域也逐渐深化与细化,因而产生诸多专题性研究,又可分为以下几项:
(一)土司制度的介绍及评价
此类文章基本上是按线性的时间序列,对桂西土司或进行制度层面的总体介绍,或以元明清三朝作断代分述,都在试图告诉人们“土司制度是什么”“土司制度意味着什么”;至于土司评价方面,在“现代”语境下,土司制度作为一种“封建社会阶级和民族压迫的工具”,对其评价强调负面性,也有基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正面声音。
(二)土官的族属问题
这是土司研究的重要论题,甚至可以联系到一些学者强烈的民族情感。讨论的焦点为土官究竟是“外来汉人”还是“本地土著”(即壮族),刘锡蕃早期主张前说,在《岭表纪蛮》中就有相关论述,黄现璠等编著的《壮族通史》也主此说。但此后主流观点越来越倾向于“土著”说,通过大量的研究,基本已成定论,大多数相关论文就是为了驳斥前者而展开的论证。
(三)改土归流研究
既然人们普遍认为“改土归流”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本身是值得研究的,在此逻辑下,讨论重点自然围绕着改土归流的“原因、过程及结果”这样预设的议题而展开,包括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变革。
(四)经济与土地问题
经济与土地问题更为复杂,要摆脱注重社会形态与经济关系的影响颇为不易,由于“桂西土司地区属于封建领主制”的论断是长期形成的定式,许多讨论都在此既定框架内进行,经济类型化的阐述、土地占有关系的揭示都与之相关。 不过也有新视野的出现,如罗树杰的系列文章,更重视具体的实证研究,材料的使用以及论述的方式有点接近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风格,
不过也有新视野的出现,如罗树杰的系列文章,更重视具体的实证研究,材料的使用以及论述的方式有点接近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风格, 此外,杜树海通过土地文书,研究广西土司地区的土地权与人身权问题;
此外,杜树海通过土地文书,研究广西土司地区的土地权与人身权问题; 蓝武、梁亚群的文章则研究元明、清代中前期广西土司地区的移民与开发情况;
蓝武、梁亚群的文章则研究元明、清代中前期广西土司地区的移民与开发情况; 唐晓涛探讨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问题;
唐晓涛探讨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问题; 李小文等研究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里甲制度。
李小文等研究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里甲制度。
(五)宗法制度研究
几百年的在地化统治,每任土司都逐渐形成血缘性的宗族世系,当然也留存下来许多族谱。日本学者谷口房男与国内学者白耀天合作搜集并整理出版了《壮族土官族谱集成》一书,是观察土司历史与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这些族谱存在着大量“攀附”汉文化的现象,编者不惜笔墨进行“打假”和“辩伪”。![[日]谷口房男、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1DC1FE/2376555620141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111477-55mT47H0SNd0tZR6d5cmWWsRPR3xXIt5-0-26a87f292c97aeb21f83c0198442766c) 蓝承恩对忻城莫氏土司的祭祖仪式进行了考证,所述甚详,可作为资料使用。
蓝承恩对忻城莫氏土司的祭祖仪式进行了考证,所述甚详,可作为资料使用。 此外,土司家族的“封建宗法形态”也受到了关注,主要讨论以“族权”为中心所衍生的各种利益关系。
此外,土司家族的“封建宗法形态”也受到了关注,主要讨论以“族权”为中心所衍生的各种利益关系。 但有关土司宗族制度的全貌研究尚属少见。笔者在《论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一文中全面介绍了桂西土司的宗族制度,并试图揭示宗族制度如何被演绎为文化和政治的象征,成为土司表达国家认同、创制汉人族群
但有关土司宗族制度的全貌研究尚属少见。笔者在《论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一文中全面介绍了桂西土司的宗族制度,并试图揭示宗族制度如何被演绎为文化和政治的象征,成为土司表达国家认同、创制汉人族群 身份、控制地方不可或缺的手段。梁亚群围绕“田州岑氏族谱”探讨该土司的国家认同问题。
身份、控制地方不可或缺的手段。梁亚群围绕“田州岑氏族谱”探讨该土司的国家认同问题。
(六)土司家族与人物研究
对某一土司家族或人物传记式的描述,似乎有一种怀古的格调,所展示的不外乎是此家族的兴衰荣辱,或此人物的生平事迹,当然也会对一些史迹进行甄别与考证。 不过,李小文的《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以一个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另辟蹊径,颇有新意,将一个俍兵家族的历史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视野,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
不过,李小文的《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以一个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另辟蹊径,颇有新意,将一个俍兵家族的历史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视野,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 至于瓦氏夫人,因其抗倭的英勇事迹而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不过大多也还只是停留在史实考察的层面。
至于瓦氏夫人,因其抗倭的英勇事迹而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不过大多也还只是停留在史实考察的层面。
(七)军事研究
其研究主要反映在土兵与狼兵,以及朝廷镇压土司叛乱等议题上。在桂西历史上,土司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是维持自身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每遇战事,朝廷就能紧急征调,常为之解忧。这一现象是研究者主要讨论的议题。此外,土司叛乱研究主要集中于嘉靖初的“思田之乱”,多侧重于事件史的描述。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视野,唐晓涛通过“狼兵”东进的视角展现明清广西浔州府复杂的社会转型与族群变迁,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视野,唐晓涛通过“狼兵”东进的视角展现明清广西浔州府复杂的社会转型与族群变迁, 她认为“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反映了明中期桂东“猺乱”、桂西土司势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历史图像。
她认为“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反映了明中期桂东“猺乱”、桂西土司势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历史图像。
(八)民间信仰研究
在土司统治期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影响深远的地方信仰系统,右江河谷的“岑大将军”信仰即为典型代表,此外,“岑三爷”信仰、“莫一大王”信仰等在原桂西土司地区也占有重要地位。黄家信在《壮族的英雄、家族与民族神:以桂西岑大将军庙为例》一文中,就明清泗城州(府)大致范围内的岑大将军庙作了统计,并简要描述了每个庙的地理分布及祭祀情况; 康中彗在《民间信仰与社会记忆——对桂西壮族岑氏土官崇拜的文化解释》一文中则试图利用社会记忆理论对岑大将军信仰的流播与传承进行解释。
康中彗在《民间信仰与社会记忆——对桂西壮族岑氏土官崇拜的文化解释》一文中则试图利用社会记忆理论对岑大将军信仰的流播与传承进行解释。 笔者在《论桂西岑大将军信仰的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一文中,将岑大将军信仰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建构置于土司“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来观察。
笔者在《论桂西岑大将军信仰的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一文中,将岑大将军信仰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建构置于土司“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来观察。 红水河流域的“莫一大王”的研究则主要偏重于文学,有学者认为此神明与当地莫氏土司无关,相比之下,宗教人类学意味的研究较少。
红水河流域的“莫一大王”的研究则主要偏重于文学,有学者认为此神明与当地莫氏土司无关,相比之下,宗教人类学意味的研究较少。 也有学者将东南亚的麽公与广西土司政权联系起来。
也有学者将东南亚的麽公与广西土司政权联系起来。![[澳]贺大卫、莫海文:《东南亚、广西西部的麽公与土司政权之关系》,《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1DC1FE/2376555620141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111477-55mT47H0SNd0tZR6d5cmWWsRPR3xXIt5-0-26a87f292c97aeb21f83c0198442766c)
(九)社会文化与族群认同
桂西土司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地方边陲的“小传统” ,更要关注它们与中央王朝“大传统”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种互动中,大传统作为“文明化”的力量改变了边陲社会文化,张江华系列文章皆聚焦于该主题。
,更要关注它们与中央王朝“大传统”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种互动中,大传统作为“文明化”的力量改变了边陲社会文化,张江华系列文章皆聚焦于该主题。 韦顺莉等研究土司社会民众的族群认同问题。
韦顺莉等研究土司社会民众的族群认同问题。
三、域外研究述评
(一)日本有关桂西土司研究![主要参考了[日]谷口房男:《日本的壮族史研究动态》,覃义生译,《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日]谷口房男:《日本民族史研究动态(续)》,谢崇安译,《红水河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覃乃昌:《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2002年第1期。](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1DC1FE/2376555620141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111477-55mT47H0SNd0tZR6d5cmWWsRPR3xXIt5-0-26a87f292c97aeb21f83c0198442766c)
一直以来,日本学者就十分重视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并逐渐发展出一批研究团队,西南的苗、瑶、壮等族是其重点考察的对象,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桂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在此背景之下而兴盛。日本学者较早地开始将人类学某些研究方法引入土司制度研究中,重视以微见著的微观视角,常通过桂西土司来讨论更大区域甚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或民族互动的状况,探讨的问题也趋于精致化,一些学者还曾来广西做过多次短期田野调查。不过总体而言,多数文章更多地表现出日本学者细致、缜密的史料使用与考证的学术传统,只见“制度”与“历史”,而较少有“文化”的影子,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的历史学范畴。
较著名的日本学者当首推谷口房男,其研究领域甚广,包括桂西土司制度的总体诠释、土司的叛乱、瓦氏夫人、土巡检司、土官族谱研究、各种文献考证等。 塚田诚之的研究侧重于民族史维度,我们可以通过其剖析壮族历史的一系列文章来认识桂西土司制度。
塚田诚之的研究侧重于民族史维度,我们可以通过其剖析壮族历史的一系列文章来认识桂西土司制度。 神田正雄、菊池秀明、野崎刚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著文阐述桂西土司制度的各种议题。
神田正雄、菊池秀明、野崎刚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著文阐述桂西土司制度的各种议题。![[日]神田正雄:《广西的土司》,王克荣译,《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4辑;[日]菊池秀明:《明清时期广西壮族土官的“汉化”和科举》,《中国——社会与文化》1994年第9号;[日]野崎刚:《论广西土司与土目——以族谱为中心》,《史峰》1988年(创刊号)。](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1DC1FE/2376555620141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111477-55mT47H0SNd0tZR6d5cmWWsRPR3xXIt5-0-26a87f292c97aeb21f83c0198442766c) 与桂西土司制度相关的研究也颇多,河源正博是早期民族史的开拓者,对后继研究有一定影响。
与桂西土司制度相关的研究也颇多,河源正博是早期民族史的开拓者,对后继研究有一定影响。![《关于左、右江流域蛮酋的始祖》,《南亚细亚学报》1944年第2期;《关于宋代羁縻州、洞的“计口给田”》,[日]山本达郎编:《东南亚政权结构史的考察》,竹内书店,1969年;《蛮酋的内徙》,《政法学报》1955年第7期。](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1DC1FE/2376555620141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111477-55mT47H0SNd0tZR6d5cmWWsRPR3xXIt5-0-26a87f292c97aeb21f83c0198442766c) 白鸟芳郎的研究虽以瑶族为重点,不过一些文章透显出大气,试图梳理出华南、西南甚至东南亚这些大的区域民族史的内在脉络。
白鸟芳郎的研究虽以瑶族为重点,不过一些文章透显出大气,试图梳理出华南、西南甚至东南亚这些大的区域民族史的内在脉络。 冈田宏二是宋代民族史的专家,对湖南和广西的瑶、壮族的社会结构及与朝廷的政治关系有较为独到的研究,注重细节的考证,如阐释广西左右江的峒丁、广西的马政都很到位。
冈田宏二是宋代民族史的专家,对湖南和广西的瑶、壮族的社会结构及与朝廷的政治关系有较为独到的研究,注重细节的考证,如阐释广西左右江的峒丁、广西的马政都很到位。 此外,小川博
此外,小川博![[日]小川博《唐代西原蛮的叛乱:华南少数民族史之一》,《历史教育》1963年第11期;[日]冈野仓子、守屋美都雄:《明代土司制度研究笔记》,《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1965年第1集;[日]冈野仓子:《明代土司制度考》,《待兼山论丛》1967年(创刊号);[日]大林太良:《中国边疆土司制度的民族学考察》,《民族学研究》1970年第35卷第2号。](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1DC1FE/2376555620141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111477-55mT47H0SNd0tZR6d5cmWWsRPR3xXIt5-0-26a87f292c97aeb21f83c0198442766c) 、冈野昌子与守屋美都雄、冈野昌子、大林太良等发表的与民族史或土司制度有关的论文,值得借鉴。
、冈野昌子与守屋美都雄、冈野昌子、大林太良等发表的与民族史或土司制度有关的论文,值得借鉴。
(二)欧美有关土司研究
从目前可掌握的情况来看,欧美学界对于中国的土司制度研究似乎多立足于整个中国或西南地区,偏重于云南,鲜有桂西土司研究的成果。在较早期论著中,赫罗尔德·威恩斯(Herold J.Wiens)通过汉人向南方迁移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这些地区的土司情况(专辟一章介绍土司制度),强调了汉人与少数民族互动、文化的碰撞以及土司制度所带来的影响等。 此外,另有部分论著都从不同角度涉及西南土司制度,亦可一读。
此外,另有部分论著都从不同角度涉及西南土司制度,亦可一读。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珍妮弗·图克(Jennifer Took)的著作以壮族土司为个案,主要讨论土司的历史与制度性问题,认为土官既作为中央王朝之内的人,又是“非汉”政体的首领,具有双重品性;同时,作者介绍了土司的社会结构,管理机制以及土地制度,改土归流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是不容忽略的一部著作。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珍妮弗·图克(Jennifer Took)的著作以壮族土司为个案,主要讨论土司的历史与制度性问题,认为土官既作为中央王朝之内的人,又是“非汉”政体的首领,具有双重品性;同时,作者介绍了土司的社会结构,管理机制以及土地制度,改土归流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是不容忽略的一部著作。
从几十年的学术回顾来看,国内有关桂西土司的研究已十分丰富,成果数量和规模不输于其他热门领域。但遗憾的是,总体而言,国内21世纪前的多数研究囿于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范式, 在理论和方法上造成的束缚与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国外学界,如日本学者的研究,正如前述,尽管有些新意,却仍然摆脱不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框架,很难提炼出有创见性的核心观点。西方学界,至今从未形成规模化与系统化的研究,亦缺乏更多个案性的作品问世。21世纪后,桂西土司研究迈入新的阶段,出现很多创新性的成果,不过相对于厚重博大的土司研究领域,还有待引入更多新视野、新理论和新方法,建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框架。
在理论和方法上造成的束缚与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国外学界,如日本学者的研究,正如前述,尽管有些新意,却仍然摆脱不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框架,很难提炼出有创见性的核心观点。西方学界,至今从未形成规模化与系统化的研究,亦缺乏更多个案性的作品问世。21世纪后,桂西土司研究迈入新的阶段,出现很多创新性的成果,不过相对于厚重博大的土司研究领域,还有待引入更多新视野、新理论和新方法,建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框架。
基于此,在反思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如何从当前较为前沿的学术领域汲取知识、素材和理论,为桂西土司乃至全国各地土司研究开创新局面,就成了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已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的“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能提供一种研究的独特路径,可借此将桂西土司研究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