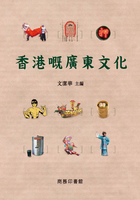
流行文化
粵語入文與雅俗界線——以1950、60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為考察對象
樊善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一
八十年代後期,羅貴祥曾提出,「語言的表達,一直都是香港文學面對的難題」,有人「取笑香港人的普通話不靈光,如何能夠寫出優秀的中文創作」,有人「歎息『港式』中文的蕪雜污染,判定香港文學難成氣候」。內地和台灣的「尋根」、「鄉土」作品揉入地方土話,「被認為是對固有土〔地〕文化的肯定和致意,也是對西方現代化入侵的一種抗衡態度。可是當香港作家企圖把廣府話(很大程度上,已與廣州使用的廣府話有差異)融入作品中時,卻往往被批評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認識、毫無中國味道或惡性西化等」。[1]時至今日,粵語入文的禁忌似乎已經打破,關夢南、飲江的新詩,黃碧雲、董啟章的小說,都嘗試過加入港式粵語,不僅沒有失去高雅文學的地位,更體現了深摯的本土情懷。可是細心一想,這裏其實有兩個問題沒有說清楚:一是為甚麼粵語所入之文」只限於新詩和小說,以夾雜方言為藝術風格或表現技巧,[2]用「港式中文」來創作散文卻未見高雅文學的支持?二是香港作家一直無法運用純正的普通話嗎?
如果不以本土意識為「香港文學」的定義,只討論在香港這地方出現的文學,那麼以粵語為母語、普通話未達流暢自如之境的作者,不見得在過去數十年都佔多數。粵語能否進入高雅文學的文類,也未必與作家的語言背景、當前所理解的本土認同相關。下文將以1950、60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為案例,探討粵語入文和雅俗文類界線的關係。
二
《新生晚報》創始於1945年12月,停刊於1976年1月,出版期長達三十年。1950、60年代之交是該報的高峰期,其聲譽主要來自副刊「新趣」版。[3]「新趣」的靈魂人物是身兼主編和作者兩職的高雄。[4]在高雄主持下,「新趣」匯聚了眾多具叫座力的小說、散文名家,如平可、南宮搏、李雨生、今聖歎、司明、十三妹;而高雄本人也化用不同筆名,撰寫各種類型的作品,或開創潮流,或後出轉精,如署名經紀拉的「經紀拉」系列小說、署名小生姓高的文言豔情小說、署名許德的「司馬夫奇案」系列偵探小說、署名三蘇的「怪論」。[5]除了武俠小說並無突出表現之外,「新趣」的多種作品類型不僅吸引了讀者,也引起其他報紙的仿效。[6]
從前面列舉的作者和作品類型,不難看出「新趣」以及受它影響的副刊,主要屬於大眾化口味,而非高雅文學。正是在通俗的刊物裏,粵語方言才得以自由進入書寫之中,發揮它的特殊魅力。[7]早期「新趣」粵語入文的作品大致上有兩類:一是連載小說,如「經紀拉」系列、阿筱《托盤私記》,二是時事諷刺詩文,如「怪論」、滑稽諧趣的新聞評點及詩詞。[8]上述作品中尤以「經紀拉」系列和「怪論」最廣為人知,高雄(經紀拉、三蘇)的貢獻自然不可忽略。
「經紀拉」系列包括《經紀日記》、《拉嫂私記》、《拉哥日記》、《飛天南外傳》等,始自1947年,在整個五十年代幾乎沒有間斷地連載,直至六十年代中期仍有餘音。各篇作者或署名經紀拉、拉嫂、拉哥等,其實都是高雄。主要角色經紀拉是一個「萬能」中介人,為不同貨物的買家、賣家居中聯繫。小說以日記形式描述主角的所見所聞,從而展示香港當時的社會百態。[9]各方面情況顯示,「經記拉」系列深受讀者歡迎,[10]但有助它建立比通俗小說更高文學地位的評論,則不成比例,其中今聖歎的〈《經紀日記》序〉可謂空谷足音。
今聖歎為《經紀日記》單行本所寫的序言盛讚高雄透徹了解香港,因此能夠像《水滸傳》那樣,「敍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為難也」。又認為《經紀日記》「承接了五四的餘波,也啟創了二次大戰以後的中國方言文學界,做了一個開路的先鋒」。[11]所謂「承接了五四的餘波」,是指小說反映、批判了時代的黑暗,又提供了同情和希望,而方言文學界的先鋒,當然是就三及第行文而言。[12]本文關注的是後者,這裏不妨選錄一段小說原文:
時已不早,我去新寫字樓返工矣,三美已經叫人來間房,一開二,自然佢間大的,我間細的,不過文具傢俬,十分摩登而名貴,完全係美國派頭,三美曰:「做我地這一行,有的不同,若果外表不摩登,人地睇起來唔開胃也。未能同自己做廣告,又點可以同人地做廣告?」此種言論,亦係老番派頭,中國佬做野,唔計者。賣花之人戴竹葉,往往如此。所以中國廚房最一塌糊塗,而我縫鋪中亦烏煙瘴氣,不過做出來之菜與衣服,世界馳名。你如果睇上(班跳舞)〔海縫師〕之衣服做貨辦,就唔使幫襯佢都得矣。[13]
今聖歎更重視的,是《經紀日記》的社會學、經濟學價值,因為此書「將近五六年來之香港社會形態,商場貿易,物資交流,以及香港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全部烘托出來,每天積累,遂成巨帙,使將來正式研究解放前後,香港的經濟社會情況的人,能得到一份連綿數年的活資料,於學術貢獻,誠不可估計」。[14]其後劉紹銘也從這一角度認定《經紀日記》屬於「以廣東方言寫成的譏世諷俗小說」,與《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一脉相承,並引述《經紀日記》原文,分析作者怎樣運用「近乎自然主義的手法」來「報道和描寫香港人情社會」。[15]劉氏的論說細緻合理,但廣東方言在小說中是否只有營造地方風味的作用,或者說粵語入文是否可能具備美感,則仍待探討。當時有論者質疑為甚麼把高雄視作嚴肅作家,與這一欠缺似乎不無關係。[16]事實上高雄也說自己只是賣文為生的「寫稿佬」罷了,作品「並無文學價值,亦無歷史價值與社會價值」,這是香港環境對寫作的限制。[17]
「怪論」是「新趣」另一種大受讀者歡迎的文類,雖然並非高雄始創,卻以他最負盛名,小思認為三蘇(高雄)「往往談笑用兵,把問題層層逼出,把人的虛偽剖破」,「銀針一枝,攻其無備,三灣四轉刺入心脾」。[18]「怪論」最有趣的是乍看來不合常情,細想之下卻含至理。高雄曾以《東萊博議》「力能舉千鈞之重,而不能自舉其身」兩句為怪論之例,另一「怪論」作者馮宏道則指歐陽修當考官時所出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也是怪題目。可見怪論古已有之,並不限於現代的方言文學。[19]如果粵語入文總算有助於小說的人物形象,那麼「怪論」不一定要塑造角色,不「純正」的行文又有甚麼文學作用?因此研究者聚焦於「怪論」作者的見解,就不足為奇了。
到目前為止,探討「三蘇怪論」的學者以熊志琴最為深入。熊氏借用余英時的說法,指古代「俳優以狂自居,實際上是用『俳諧怒罵』的方式說實話」,又引述1917年上海《申報·自由談》濟航的〈遊戲文章論〉,認為文中「雖有忠言讜論載於報章,而作者以為遇事直陳不若冷嘲熱諷、嬉笑怒罵之文為有效也」之語,「正正說明了『怪論』以『怪』立言的原因和意義」。[20]熊氏再以三蘇〈我怎樣寫怪論?〉來印證:
我向來是不把怪論作為「怪誕之論」看的。我說的只是真實。我自問寫怪論的心情,其嚴肅的程度與寫社論無異。
又:
在這一加一等於三,打勝仗變了打敗仗的世界,以及在「寧可獻金鑄像不成,卻不肯行款教濟那些眼看餓死冷死的人」的社會之中,是往往變了非,非變了是,真實變了狂妄,狂妄變了真實,哭變了笑,笑變了哭,把事情說穿了,於是乎就變成了「怪論」。[21]
熊氏強調「怪論」所說的是「實話」,而採取嬉笑怒罵的方式是為了更「有效」,這當然很準確。但為甚麼「怪論」比「正論」有效?濟航〈遊戲文章論〉其實已有答案:「雖有酷吏力無所施,言者既屬無罪,禁之勢有不能,則其心自潛移默化。」[22]這也正是俳優「用『俳諧怒罵』的方式說實話」而不敢直言其事的原因。三蘇的自白文章把「怪論」和「社論」等量齊觀,其實只在寫作心態上,而不是指表達手法。該文的收筆說:我希望有一天沒有一個人喜歡看怪論,大家說的也是怪論,那時我可以不必寫怪論了。那一定是一個好世界,我相信。」[23]這幾句未免有點怪論味道。港英殖民政府自始就沒有開放管道讓一般市民參與決策,三蘇寫此文時情況還好,1949年後在東西冷戰的嚴峻局勢下,更收緊了言論和出版的規管。[24]權力不對等並不限於政府和市民,社會上有勢力者也可訴諸法律禁制對他們不利之言。[25]在這種情況下,更無法不多用曲筆了。
可是佯狂以免禍只是選用怪論這種表達形式的一個原因,這些文章都發表在商業媒體上,迎合讀者興趣顯然是另一重要考慮。[26]前者是以一種低下的文類作掩護,以收「大人不記小人過」的效果;後者既然以金錢利益為重,在一般人看來,文學價值就很成疑問了。無論出於作者的本意或是附隨的副作用,總之,「怪論」雖然是另一種大受歡迎的粵語入文作品,卻終究不屬於高雅文類。[27]
真正在高雅文類使用粵語的是散文作家十三妹。十三妹1958年中在《新生晚報》的另一個副刊「新窗」版開始寫散文專欄,翌年轉到「新趣」才逐漸建立聲名,一年多後主編高雄提議她把專欄更名為《十三妹專欄》,據說是香港報紙副刊上第一個以作家名字作標榜的專欄。[28]十三妹不是廣東人,她的專欄並非「三及第」文章,而是以白話文為基礎,刻意引入粵語,例如一篇談Irving Wallace長篇小說The Prize的專欄,文中用粵語翻譯了一句話:
你呢支〔隻〕衰嘢,快的著番條袴,即刻返落來。
十三妹說是因為「一涉粗俗,就非動用廣東話不可了」。[29]但不止是「粗俗」話才用粵語,例如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Reconsiderations,她竟別開生面地譯作《要諗過一排》。[30]十三妹使用的粵語遠不及高雄那麼多,不過她一再說明粵語入文的必要:
十三妹,自從來售此類之稿,開始注意與學習廣東話以來,對於粵語系之文法構造與詞彙,即大為捧場,許之為中國從北到南,所有各種全國性或地方性的體系之中,最富有聲光與色彩之妙者。此一發現與捧場,數年以來,雖經行內行外,自大雅君子以至居心匝〔叵〕測輩之反對與抨擊,然對於廣東人口裏的廣東話,欣賞讚歎之心,敬佩熱衷之情,未嘗稍減者焉![31]
其實十三妹除了認為粵語豐富多姿,勝於北方俗語外,還把用語的選擇理解為能不能追上時代。事緣一位署名「長者」的讀者寫了一封長信給十三妹,說粵語入文並不高雅,勸她以後不要這樣寫,十三妹從兩方面回應,一是質疑目前反對粵語入文的人並不反對以某些地區的方言入文,這是否表示入文的俗話「只能局限於黃河流域之系統,而不能採納粵語系統」,在她看來粵語要比黃河流域的俗話更豐富多變;二是認為從俗意味追隨時代潮流,「自聯合國大會上的代表們口頭的語文,以至獲『諾貝爾文學獎金』的作者的文字,已今非昔比,都是以俗入文的了」。十三妹總結說:
從來輕蔑剽竊摹擬與抄襲。祖先遺下來的東西,是祖先們創造出來的,我們一樣的腦子,為甚麼不能創造因時制宜的新東西新字眼?何況揚棄一些年代太久遠的表現交換我們的思想情感的方法與工具,是與今日已被先進國家若歐美採取於編纂字典的實際步驟。[32]
高雄和其他三及第作家似乎從來沒有把粵語的地位看得這麼高。
十三妹寫作生涯的全盛期只有在「新趣」那四年多,1964年離開《新生晚報》就逐漸低沉了,[33]1970年更淒涼離世。由於直至最近作品才首次結集成書,中年以下的讀者大多對她沒有甚麼印象。不過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十三妹專欄以淺白語言介紹西方文化,對不少渴望追求新知的青年讀者饒有啟蒙之功,這由她去世時《中國學生周報》頭版的悼詞可見一斑:
本報現存編者及大部分老作者,在求學時期均曾是十三妹女士之忠實讀者,所受影響,不云不深。[34]
三
美國社會學家第馬久(Paul DiMaggio)研究社會結構、藝術生產和消費模式、藝術的分類系統三者的關係,指出一個社會的羣體結構反映在它的藝術分類系統上,因為社會不同的羣體需要通過欣賞、參與特定門類的藝術來自我定義,並確定誰是羣體的成員。他認為藝術分類系統可以在四個層面上變化:分化(differentiation)、層級(hierarchy)、普遍性(universality)、界限強度(boundary strength)。分化指藝術門類是否愈分愈多,層級指藝術門類有沒有高級和低級之分,普遍性指不同社會羣體評定藝術門類高下的標尺是否相同,界限強度指不同藝術門類可否越界(例如一個藝術家從事兩個門類的藝術、一種藝術門類挪用另一種藝術門類的某些特色)。這些變化的動力來自社會結構的轉變,但社會結構不會直接影響藝術分類,而是以藝術生產模式(包括商業、專業、科層三種)為中介,例如以商業原則為主導的藝術生產模式,為了爭取更多顧客,會盡量降低藝術產品的分化程度和界限強度;相反,以專業原則為主導的生產模式,藝術成就由行內人判定,藝術家就努力發展新的形式來突出自己,從而增加分化程度。[35]
相對於以往的社會學家多從藝術內容來探討社會意識,第馬久可謂另闢蹊徑。他用來理解藝術分類系統的的框架,由大量研究美國社會的個案綜合而成,稍加剪裁不難移用於其他社會。[36]台灣學者林芳玫即利用第馬久的框架,結合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rudieu)的「文化資本」概念,論證1980年代台灣文化界熱烈討論、批評通俗文學,是一種「象徵性權力鬥爭」(symbolic power struggle)。林氏的意思是,八十年代在台灣興起的文化工業,「動搖了知識分子的既定位置,侵蝕、襲奪知識分子在文化方面的掌控權,開闢出學院以外的廣大文化場域(即大眾文化),在此聚集了龐大的資源和權力」,前述的討論、批評就是知識分子和文化工業對誰有權判斷文類雅俗的鬥爭。[37]「新趣」版上粵語入文的現象,一度由低級文類(連載小說、怪論)擴展至高級文類(散文),也可以藉助第馬久的框架來解釋,林芳玫所運用的布迪厄「文化資本」概念,尤其足以說明轉折的關鍵。
回到香港粵語入文現象的變遷,據歷史學者程美寶的研究,晚清時期粵語出版物的市場不可小覷,但「粵語寫作始終離不開娛樂、傳道、教育婦孺的範圍」,即使在廣東人心目中,粵語寫作的地位仍是邊緣的。[38]光緒末年康有為的學生陳子褒在澳門、香港開辦私塾,用粵語編寫蒙學教科書,但這只是便利初學者,陳氏認為升上中學就該學習國語了。[39]及至民國成立,白話文運動也成為建立新政體、新制度的一環,由各地提倡當地的白話,變成全國提倡以北京音為標準的白話,粵語寫作逐漸式微。[40]另一位研究者李婉薇則指出,辛亥革命後,龍濟光管治廣東,強調尊孔,同時部分傳統文人移居香港,港英殖民政府為鞏固統治而扶植復古文化,省港兩地都籠罩在舊文學勢力之下。北京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力伸展到廣東後,「二十年代的廣州和香港成為文白的戰場」,在文言與白話二元對立的論述中,方言幾無立錐之地」。[41]自晚清以來,粵語作品寫得怎樣考究,都難以攀上高雅地位。以香港出版的《小說星期刊》為例,該刊1924年9月27日創刊號的目錄分為「論壇」(論說文)、「說薈」(小說)、「翰墨筵」(唱酬詩文)、「劇趣」(有關戲劇的詩文)、「談叢」(散文)、「諧林」(笑話)等類別,前五類是嚴肅的議論或正統的創作,文言、白話皆有,粵語入文的作品只見於「諧林」,[42]可見粵語只能在低級文類中使用。1947年香港的左派文化人曾有一次關於怎樣利用方言文學宣傳革命的爭論,熱鬧了幾個月,實際成果中只有黃谷柳的《蝦球傳》成績稍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統一政策取代了地方主義,不再提倡地域性文藝,粵語入文只能在香港發展了。[43]
上一節介紹了「經紀拉系列」、「怪論」和十三妹專欄的粵語入文特色,如果結合當時報刊文學的情況,就可以發現文類區分系統(相應於第馬久的「藝術分類系統」)正經歷深刻的變化。在《經紀日記》之前,新趣」的連載小說不出偵探、艷情、奇情、言情、歷史等類型,一般報紙副刊也是如此。《經紀日記》和這些類型最大的不同,是取材自當前社會的日常生活,角色都是隨處可見的普通人,儘管情節發展不見得真實,卻也不以奇詭或纏綿吸引讀者。《經紀日記》的成功催生了大量類似作品,在原來的連載小說文類中「分化」出新的類型。「怪論」雖然不是高雄所創,但以他最負盛名,把一種次要文類推廣至路人皆知,後來者往往模仿他的三及第行文和刁鑽角度,可說接近於新類型的「分化」。今聖歎、劉紹銘等評論者,從學術角度肯定《經紀日記》的成就,連帶它所屬的文類也提升了「層級」——報紙連載小說不見得就沒有價值。但這只是某些人的看法,未有社會「普遍性」,高雄也只以「寫稿佬」自稱。[44]最後是十三妹,在她看來粵語傳達新知識的功能有時甚至勝過白話文,高雄的粵語入文只限於連載小說和滑稽諷刺兩種低級文類,十三妹卻成功地降低了散文這種較高級文類的「界限強度」。
第馬久框架的基本原理是,社會結構以藝術生產模式為中介,投射於藝術分類系統上。上述文類區分系統的變化,正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社會結構轉型,施諸商營報紙副刊的影響。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為中國內戰、政局、天災等,內地大量人口湧入香港,趨勢持續了整個五、六十年代。外來人口激增使得香港變成一個陌生人的社會,「經紀拉系列」和其他反映社會百態的小說,不僅教導讀者怎樣理解身處的地方,還巧妙地利用情節的轉折暫時緩解了大眾的焦慮,以保持社會安定。[45]「怪論」同樣有點出作者心目中社會真相的功能,「曲筆」而非「直言」的寫法,就作者而言固然有免觸禁忌的用心,就讀者而言誇張滑稽的表達更能宣洩無可奈何的不滿。
這一時期移入的人口為香港提供了廉價勞工、技術人才以及資金,但也有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香港無法找到和教育資歷對應的工作,[46]幸而恰值香港社會迅速增長,報業隨之而大幅擴張,於是得到執筆撰寫小說或專欄以維生的機會。這些人不僅壯大了報紙作者的陣營,他們大江南北的背景也埋下了使副刊面貌變得多元化的種子,十三妹就是後來開花結果的一位。[47]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年人口比例遠較目前為高,據1961年的政府人口統計,十九歲以下青年和兒童佔總人口46.71%,[48]但學額遠不足夠。適齡入讀小學的兒童(6至11歲)共五十萬人,在學者只有三十一萬人,小學畢業後有機會升上中學的,更只有20%至25%。[49]正規教育機會不足,使得青年渴求通過其他途徑獲得知識。此外,在五十年代以前,香港社會較歡迎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中學,或直接回內地就學,以便銜接國內的高等教育,日後有更廣闊的出路。1949年國內情勢大變,這種想法開始逆轉,特別是在1952年中共的統治穩定下來之後,香港中、英文中學數量此消彼長,從此崇尚英文和西方的心態貫徹到教育體制。[50]十三妹常鼓勵寫信求教的青年學好英文,又以很少專欄作者能夠像她那樣直接閱讀西方書刊而自豪,[51]這些言論都可以在當時社會環境找到解釋。
最後,從二戰結束到六十年代末,除了韓戰暴發初期,香港經濟平穩上升。[52]儘管最富裕的階層可能是從江浙移居的工業家,[53]但本地人口畢竟以廣東人佔多,粵式口味的消費市場不容忽視,高雄粵語作品的風行顯然受益於此。[54]
社會結構的變化,在一份商營報紙看來,顯然是難得的獲利契機。高雄憑着社會觸覺和寫作才能成為有口皆碑的編輯和多種流行文類的領袖,似乎順理成章,十三妹的故事卻更能突顯「粵語入文」的發展和限制,既有偶然的機遇,又無法離開社會因素。
四
「經紀拉」系列的作者高雄和評論者今聖歎、劉紹銘等合力提升低俗粵語文類的地位,十三妹則在相對而言較高雅的散文文類中引入粵語。有趣的是,十三妹的母語不是粵語,卻提倡粵語入文;本來不想當作家,卻賣文成名;沒有正式學歷,卻以普及西洋知識建立了聲譽。這一連串的錯位,原來並非互不相關。
根據十三妹的自述,她生於越南河內,父親是越南華僑,母親是北京人,她本人曾在越南、中國、印度等地居住,自小學習法文、英文,中文則非正式地學自乳母。十三妹沒有讀過大學,但家裏為她聘請補習教師,學習音樂和其他知識。1949年內地易幟,當時家人已經過世,十三妹孤身來到香港。最初在商業機構工作,其後當上鋼琴教師,但因為患病無法繼續,改為向報紙投稿,經過幾年努力終於成為專欄作者。十三妹不與同行來往,即使長期合作的編者如高雄、劉以鬯,也沒有見過她,有些人因此把她渲染為神秘女作家。但十三妹多次在專欄中表白,這只是因為她不屑與職業作者為伍。在她眼中,職業作者最嚴重的缺點是依賴關係而不是作品的素質來換取稿費,她本人則相反,「也只有《新生〔晚報〕》,才容納得了十三妹這樣上不沾天下不落地,既不服左也不服右,純然靠票面的招牌」。[55]
十三妹完全不認同文壇常見的結盟方式,也無意遵從報紙散文的寫作慣例,但她那種副刊上罕見——甚至可以說前所未見——的作者形象(對任何人都不賣賬)和文章內容(大量西方現代知識),終於令她闖出名堂:
由於這近一年來之大膽嘗試,卻也有了些收穫。而收穫中之最著者,率直書之,就是改變了一些本版編者的成見。[56]
這「成見」就是副刊必須以通俗趣味為主。隨着名聲日著,十三妹更把自己的寫法說成是一種應時而生的新模式:
我們的時代,節奏如此其緊,於是自必影響文章。猶若一道河流,滔滔滾滾,泥沙碎石微生物,哪來得及為之一一換出釐清?我們的思想感情,四面八方而來,甚麼來到筆下就寫將出來,此之謂曰專欄文章,蓋作者之所思所感所受者也。
又:
所以,十三妹的下欄之文,一貫以泥土沙石微生物夾雜其中為特色,我甚至不但不會為此一特色而自愧,決不想為此改變作風,而且自信此乃七十年代之特色。[57]
這篇文章刻意反用沙石、微生物的象徵,把傳統寫作視為雜質的元素——粵語當然包括在內[58]——重新定義為現代化的表現,創造了一種評價散文的新標準。十三妹在另一處更把粵語視為「專欄文章」現代性的要素:
昨於此談「下欄」之出現地方語文,還忘了指出一點基本上之要求。蓋此類之文,以其時間空間性甚強,並非準備留之於世者,(當然,那些自負良深,更妄以為有警世、喻世、諷世之井底蛙文則不在內)故自題材以至表達之方式,包括所使用之詞彙在內,在原則上是要求新鮮變化的。所以,我覺得這類的文字,作者無論如何得創新手法,□一些新字彙過來,至於那些活潑潑存生於周圍的,更不能放過。於是就得個「雜」字,猶若有第八藝術之稱的電影一般,必得合許多部門,才能闢出一種新風格來。而近代語文之無法淨化,此由西方報刊文字亦可得證明。自小說以至專欄文字,穿插第二三種語文者已不可免,如文章為英文,但作者撰者在西歐者,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皆必然出現。所以何能要求宗於黃河流域語文之我輩,筆下能不吸收粵白?[59]
對當日的讀者來說,這段話最有力的是以當代西方情況為支持粵語入文的理由——在讀者心目中十三妹的威權正來自她了解當代西方世界。[60]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術語來表達,十三妹基於她的生性(habitus),找到了把文化資本轉換為象徵資本及經濟資本的方法,成功地在文學場域佔據了一個位置。
不過十三妹的生性和文化資本,在當時的香港可謂絕無僅有,後來者不大可能重演她的歷史。十三妹在「新趣」的後期,該版增設了一些談論西方現代知識的專欄,例如陳之藩《旅美小簡》、胡菊人《旅遊閑筆》和《讀書閑筆》,似乎是有見於讀者歡迎十三妹的題材。十三妹離開「新趣」後,又有由戴天、劉方(羅卡)、陸離、李英豪合寫的《四方談》專欄,另一個副刊「生趣」則有西西談中外電影的《開麥拉眼》,但這些專欄也都沒有自覺地使用粵語。[61]考察這些作者,陳之藩當時並非居於香港,戴天在毛里求斯出生,在台灣完成大學教育。二人之外,胡菊人、劉方、陸離、李英豪、西西都在香港完成中學教育,有些更取得師範或專上學歷。這些成長於香港的作者粵語應當遠比十三妹流暢,但都不曾提倡粵語入文,原因或出於香港的教育制度。
香港教育司署1950年代初頒佈的〈小學國語科課程〉規定,國語(即中國語文)課本的內容,小一至小三「全部以教授語體為原則」,小四至小六「側重語體文之教授,惟得酌情選授淺易文言」。這裏的「語體文」指白話文。語文教學包括「聽」、「讀」、「寫」、「講」等方面,「國音一科,原為統一中國各地方言而設。本港實際情形既有異於國內;各就學兒童均習慣以粵語交談;教師之講授,亦多以粵語為之。加以難獲適合之教師指導,故國音一科暫不擬作硬性之規定」。[62]所以,小學的中國語文科,講授一般雖用粵語,但讀和寫則以白話文為要求。小學如此,中學和大專也無二致。十三妹在1963年的專欄即提到,教育司署公佈——其實是重申——「教學語言以粵語為主,惟寫作時則以國語語法為據。不得雜以粵語語法」。[63]儘管有人批評教科書的白話文不通,[64]但白話文作為教育司署規定的學習內容,則向來沒有受到挑戰。在整個五、六十年代,大部分在香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如果要通過閱讀和書寫進行文化認知、交流,使用的大抵是以白話文為基礎、不自覺地摻進若干粵語、文言及其他成份的書面中文,直到近年才似乎有點變化。正是因為小學、中學以來教育體制設下的價值觀念深入人心,連《四方談》作者之一、十三妹熱心讀者的陸離,竟也沒有想到要發揚十三妹的粵語入文主張。
五
從五六十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看來,粵語能否進入高雅文類,與作者的母語無關。如果說粵語代表廣東文化重要的一部分,當年廣東文化的熱心擁護者原來包括一些並非廣東籍的人,可見廣東文化並不以母語羣體為界限,這意味當時的廣東文化對中原文化並不是抗衡、自保,而是吸納、融合。
在語文和文學上,這種優勢只維持了非常短暫的時期,以後粵語仍舊給排除於高雅文類以外。近年有些公認的嚴肅文學作者嘗試把粵語寫入新詩、小說裏,但粵語仍然沒有進入高雅的散文中。胡適認為能用白話寫詩,才表示白話文成功取代文言,其實用白話文來說理、表達知識,困難不在寫詩之下,朱自清盛讚胡適的白話長篇議論文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陳平原說朱氏「討論白話文學的成功,舉的卻是胡適的長篇論文,表面上有點錯位,實則大有見地」。[65]粵語入文也可以這樣類比,如果散文也能自由運用粵語,那才表示粵語的表現力、思維方式、文化地位得到認同,這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恐怕是無法想像的。而教育制度也還不是最深層的原因,政治、經濟、文化……比教育制度更為關鍵,但這些已不是本文能夠討論的了。
[1] 羅貴祥:〈少數論述與「中國」現代文學〉,羅貴祥:《他地在地:訪尋文學的評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頁127-128。
[2] 有些劇本為方便演出,直接用粵語撰寫,本文討論範圍只限於完全用來閱讀的文類,不包括劇本。
[3] 《新生晚報》和「新趣」版較詳細的介紹,可參拙文〈閱讀香港《新生晚報·新趣》1951年的短篇故事——管窺「香港意識」的生產和傳播〉,樊善標、葉嘉詠編:《陌生天堂:五十年代都市故事選》附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頁339-341。
[4] 據劉紹銘的〈高雄訪問記〉,高雄是「新趣」的創版編輯,一直做了十多年,見熊志琴編:《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附錄,頁282。1960年2月25日「新趣」版有一則三蘇〈代郵〉:「何水申先生:鄙人因病請假,數月未理本版編務。以後來示,請逕寄新趣編輯先生,幸勿書弟名,以免稽延時日為感。」推測高雄大概在1959年底離職。
[5] 「新趣」早期的怪論專欄名為《怪論連篇》,由多人合寫,高雄的化名除三蘇外,還有吳起、曹二家等,其他作者包括梁厚甫(筆名馮宏道)、劉國鈞(筆名連容蘇)等。
[6] 例如《新晚報》邀請高雄在該報「天方夜談」版以石狗公筆名寫類似《經紀日記》的《石狗公自記》(1954年2月12日至1966年9月30日)。高雄以史德筆名在他報寫偵探小說,則是因為許德由《新生晚報》專用,見劉紹銘〈高雄訪問記〉頁282-283。另外《新晚報》、《成報》、《明報》等都繼《新生晚報》而設立「怪論」,《大公報》「小說天地」版夢中人的《懵人日記》(1955年8月1日開始連載),顯然也受《經紀日記》啟發。
[7] 本文討論的「粵語入文」大部分是所謂的「三及第」,即雜用白話、文言、粵語,有時甚至加上英語音譯詞。另外,所謂「自由進入」,意指並不僅僅限於吸納粵語詞彙,也可以使用粵語句法。
[8] 必須注意,「新趣」更多是純用白話的長短篇小說、雜文。此外,本版早期也有文言長短篇小說、傳統風格的舊體詩詞。多種語體並存於一個版面上,也是當時報紙副刊的典型面貌。
[9] 「經紀日記」系列的詳細介紹可參熊志琴編:《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前言」頁13-15。
[10] 長期連載固然是受讀者歡迎的證明,此外,1953年大公書局出版了《經紀日記》第一、二集的單行本,1950年更有三家電影公司拍了三部改編《經紀日記》的電影,參熊志琴:《經紀眼界》「前言」頁13。他報邀請作者撰寫類似形式的小說及其他作者的仿效,也都是明顯的證據。
[11] 轉引自熊自琴:《經紀眼界》附錄,頁273-274。原刊於「新趣」1953年3月27日,後收於大公書局出版的《經紀日記》。今聖歎原名程靖宇,1948年由天津移居香港,1951年在新成立的崇基學院講授中國通史,其後任教於不同大專院校。程氏也是多產作家,今聖歎是他在《新生晚報》開始寫作時所用的筆名。程氏生平資料可參李立明:〈採稆堂主今聖歎〉,李立明:《香港作家懷(第一集)》(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0),頁214-219;今聖歎:〈採稆文存自序〉,今聖歎:《新文學家回想錄(儒林清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頁1-2。
[12] 今聖歎〈《經紀日記》序〉:「經紀拉的思想和哲學,實在是永遠跟隨着他的時代向前邁步的,他嗅到了地獄中的霉臭陰毒的氣味,他看見一切惡鬼冤魂的殘骨腐肉,把它們寫成這樣一部自己的時代的傳記。他和盤把這時代的一切托了出來,譏諷的反面是溫暖與同情。幽默給善與真理以溫暖,給惡與虛偽與欺詐自私與刻薄以無情的打擊。」見熊志琴編:《經紀眼界》頁274。這當然是今聖歎對「五四傳統」的理解。
[13] 《拉哥日記》1957年12月22日,轉引自熊志琴編:《經紀眼界》頁177。中括號內文字據「新趣」原刊改。
[14] 熊志琴編:《經紀眼界》頁274。
[15] 劉紹銘:〈經紀拉的世界〉。此文原是劉氏〈高雄訪問記〉的前言,兩者都刊於香港《純文學》第30期(1969年9月),後收入林以亮等:《五個訪問(》香港:文藝書局,1972年),這裏轉引自熊自琴:《經紀眼界》附錄,頁299-300。
[16] 李國威〈《純文學》的三蘇訪問〉:「一個人,這些年來,賣文為活,不懷文學創作的『英』心,卻讓人翻起舊帳,大做文章,是否一種挖苦?一種諷刺?抑或是鼓勵?」李國威:《李國威文集》(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頁31。
[17] 劉紹銘:〈高雄訪問記〉。引文見熊志琴編《經紀眼界》頁295。高雄在〈訪問記〉中又說:「我以為香港事實上的確只有『通俗小說壇』而沒有『文壇』。當然這和整個地方的文化氣氛有關係。這裏居住的人,整日忙來忙去,需要的只是通俗小說,於是這個地方便只能有通俗小說的市場而不可能有文學作品的市場了。〔……〕我自己從開始寫作直到現在,從未曾自以為是一個甚麼作家。我以為我只是一個俗語所講『寫稿佬』,一個『說故事的人』。勉強加上『職業』二字叫做『職業作家』亦未嘗不可,因為既加上『職業』兩字,其中辛酸,亦可想而知,雖云『作家』,與一般所謂『文學作家』,固有不同也。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稱做『作家』,我聽了只有難過。我覺得,我寫的那些東西,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同上書,頁288-289。
[18] 小思(盧瑋鑾):〈想念三蘇先生〉,小思《人間清月》(香港:獲益出版事有限公司,1996,3版),頁25-26。
[19] 馮宏道:〈憶亡友·談怪論〉,載《新聞天地》週刊,第2057期(1987年7月18日),頁25。
[20] 熊志琴:〈從羣眾中夾,到羣眾中去——《新生晚報》「怪論」與香港文化主體性〉,載《香港文學》,2009年5月號(總第293期),頁27-28。余英時的說法見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兼論「俳優」與「修身」〉,載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頁71-92。濟航〈遊戲文章論〉轉引自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載《二十一世紀》,1993年10月號,頁39-51。
[21] 熊志琴:〈從羣眾中夾,到羣眾中去〉頁27、28。三蘇原文刊於1946年12月23日的「新趣」,為該版一週年紀念而寫。
[22] 轉引自熊志琴:〈從羣眾中夾,到羣眾中去〉頁27。
[23] 轉引自熊志琴:〈從羣眾中夾,到羣眾中去〉頁28。
[24] 例如在國共內戰尾聲的1948年,香港政府開始頒佈及修訂「教育條例」、「社團條例」,以限制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參陸恭蕙:《地下陣線》(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頁85-86。又,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在眾多限新聞自由的條例中,以1951年5月制定的《刊物管制綜合條例》全面及苛刻〔……〕任何報刊會導致他人犯罪、支持非法的政治團體、影響公共秩序、健康或道德者,法庭可根據律政司申請查禁或暫停違例報刊出版6個月。此外,任何報刊惡意散發可能導致公眾不安的虛假消息,即屬違法。此例還規定不得發表任何煽動正常社會秩序的言論。」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頁527。1952年5月5日《大公報》以刊載政治煽動文字,被判停刊六個月,但後來減為十二日,參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〇——一九六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33。
[25] 例如「新趣」版專欄作者田耕的掌故文章〈陸祐的故事〉、〈關於陸祐記載(〉刊1962年4月23、24日)被陸氏後人指內容不實,發律師信警告,該版在7月9、10兩日刊登〈道歉啟事〉,同時終止田耕的專欄。
[26] 〈高雄訪問記〉:「其實寫社論,寫怪論,還是差不多?都是社會批評,不過一者板起面孔,一者嘻皮笑臉,而讀者卻只歡迎怪論,不愛社論,方式不同,後果各異,這真是無可奈何。」見熊志琴編:《經紀眼界》頁296。
[27] 高雄在《三蘇怪論選》(香港:作家書屋,1975)的代自序〈不該出版的書〉說:「這是一種遊戲文字,無非博讀者一粲,根本毫無價值可言。」(頁1)他接受劉紹銘訪問時則說,自己的作品最喜歡「怪論」(見熊志琴編:《經紀眼界》頁296)。「怪論」畢竟結集出版了,顯見序言是門面話;門面話要這樣說,也足以證明「怪論」的文學價值沒有得到認可。
[28] 十三妹作品及相關資料可參拙編:《犀利女筆——十三妹專欄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及拙文〈本命、前世與分身——作家十三妹的筆名與發表場地考〉,載《百家》,第10期(2010年10月),頁65-78。
[29] 「新趣」《十三妹專欄》〈讀以「諾貝爾獎」為題材的小說第一章〉,1963年8月31日。
[30] 「新趣」《十三妹專欄》〈聞湯恩比之巨著“RECONSIDERATIONS”已出版〉,1961年5月11日,又見樊善標編:《犀利女筆》頁206-209。
[31] 「新趣」《十三妹專欄》〈為廣東人士的借喻天才再喝一場采!〉,1963年6月6日。
[32] 「新趣」《十三妹專欄》〈且說這條牛已被拉到了樹下〉,1963年1月8日。
[33] 十三妹在1964年7月19日後不再在「新趣」版寫作。
[34] 《中國學生周報》,第953期(1970年10月23日)。
[35] Paul DiMaggio, 'Classification in Art,'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 Vol. 52(August: 440-455).
[36] 即使是美國社會,也需要因應現實修訂框架各部分的關係,例如上文轉述第馬久的說法,在以商業原則為主導的藝術生產模式下,產品的分化程度和界限強度將降低,是八十年代的情況。隨着新的生產技術、銷售管道等出現,目前可能有所不同。
[37] 林芳玫:〈雅俗之分與象徵性權力鬥爭——由文學生產與消費結構的改變談知識分子的定位〉,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6期(1994年3月),頁55-78,引文見頁58。
[38]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163。
[39]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頁157-160。
[40]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頁162。
[41]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頁331-332。
[42] 例如若夢女史〈說鬼〉:「多均鬼賦。帶荔披蘿。稽子驚鬼。吹燈滅火。遂使鬼谷先師。終日鬼頭鬼腦。而壞鬼學士。在朝在野。無非鬼叫鬼揸。」(全刊無統一頁碼)但「諧林」中也有不少純用文言的作品。
[43] 參黃繼持:〈戰後香港「方言文學」運動一些問題〉,黃繼持:《文學的傳統與現代》(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8),頁158-172;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三人談〉,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學資料選(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頁12-16。又,黃仲鳴:《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香港作家協會,2002)是這一課題資料最完備的論著。
[44] 「新趣」版董千里《人間閑話》〈方言入文章〉:「香港寫方言小說的第一枝筆自屬本刊的前任編者,但我們以為他用普通話寫的小說只有更好(此點文化界朋友均有同感)。〔……〕我這人有點頭巾氣,至今力求避免在文字中羼入任何方言,認為文還文,語還語,兩者是不應該也不必混雜的。」(1962年8月4日)
[45] 詳細論證可參拙文〈閱讀香港《新生晚報·新趣》1951年的短篇故事〉。
[46] 在當時反映社會百態的小說裏也可以找到這種題材,「新趣」有一個短篇〈醫生改業記〉,寫一個醫生來到香港,因為學歷不獲政府承認,只好黑市執業,甚至改稱中醫。見樊善標、葉嘉詠編《陌生天堂》頁46-49。
[47] 參拙文《犀利女筆·前言》頁16。
[48] 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的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報告」數據計算,當年十九歲以下青年和兒童佔總人口20.08%,參以下網址:http://www.bycensus2006.gov.hk/tc/data/data2/index_tc.htm(2013年1月2日檢索)。
[49] 譚維漢:〈二十五年來的香港教育〉,載牟潤孫等:《星島日報創刊廿五周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星系報業有限公司,1963年印刷,1966年發行),頁146-147。
[50] 譚維漢:〈二十五年來的香港教育〉頁147-148。
[51] 本節和下一節十三妹的原文書證和相關論證,如不另外說明,皆見拙文〈案例與例外——十三妹作為香港專欄作家〉,樊善標編:《犀利女筆》附錄,頁336-372,本文不再重複。
[52] 參饒美蛟:〈香港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371-416。
[53] 丁新豹:〈移民與香港的建設和發展——1841-1951〉,載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與文化:香港史公開講座文集》(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05),頁39-40。另參黃紹倫著、張秀莉譯:《移民企業家:香港的上海工業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4] 董千里〈方言文章〉:「所以使他非用方言不可者,自是買主的要求。這些買主們已在不知不覺中殺害了一個好作家,不錯,他因此有了洋房和汽車,但一個作家的份量豈是可用房子和車子來衡量的?」,「新趣」版董千里《人間閑話》專欄,1962年8月4日。但高雄的三及第小說讀者不限於廣東人,「新趣」《初白廔雜寫》專欄作者初白〈土語文學〉:「據筆者所知,非粵籍的外省人士對於這『拉哥文體』發生興趣之濃,遠比我們為甚。他們在貫通了以後,還在極力摹擬,互相引用,現在外省籍者嚐用這種文體的,竟比粵籍者為多,在本地的文壇上起了浪潮,無論左右派的報章都樂於引用,甚至時評中,標題上,也用起廣東土話來。」(1956年10月5日)所說的「時評」不知道發表在哪些刊物上?如果是大報上的嚴肅評論文章,那麼粵語進入高雅文類的時間還可提前。又,同月25日初白〈舊文抄〉延續話題,引錄了二十多年前《循環日報》上香港總督金文泰的〈提高中文學業〉演說詞。該演說詞全用粵語,開始的部分如下:「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學業,周爵紳、賴太史,今日已經發揮盡致,毋庸我再詳細講咯,我對於呢件事,覺得有三種不能不辦嘅原因,而家想向列位談談。」作者在引文後說:「這種完全口語的報導,在當時也是很特殊的。大約因為這位總督金文泰是素以精通粵語和中國舊學見稱,報章上為了特表揚起見,故將他演講時的口語照錄,是非常少有的,想不到事隔二十餘年的今日,卻會大行其道。」
[55] 「新趣」《十三妹專欄》〈吃黃蓮冷暖自家知〉,1963年3月16日。
[56] 「新趣」十三妹《一葉集》〈果真是夏蟲不足以「語冰」乎?〉,1959年10月27日。
[57] 「新趣」《十三妹專欄》〈從行家使我發嘔想換版頭名稱談開去〉,1962年8月14日,又見樊善標編:《犀利女筆》頁238-239。
[58] 「下欄」原是港式粵語,意謂無足輕重,這裏用作自己專欄的謙稱。
[59] 「新趣」《十三妹專欄》〈關於文字運用〉,1963年1月9日。案:本篇延續上文所引〈且說這條牛已被拉到了樹下……〉的話題。原文有一字模糊不清,現□號代替。
[60] 但十三妹不是深思熟慮才立論的作家,在不同的話題上,她常有反覆猶豫,例如她因為某報一則她不理解的粵語入文新聞標題,動搖了過去的想法,認為「今後應該好好的想一想這個問題了」,見《十三妹專欄》〈粵語入文的迷惑及其他〉,1963年8月15日。
[61] 陳之藩《旅美小簡》在1963年6月9日首刊,當時陳之藩《旅美小簡》單行本已在台灣出版,「新趣」只是轉載,不是直接向陳氏約稿。胡菊人《旅遊閑筆》在1963年12月14日首刊,《讀書閑筆》在1964年8月1日首刊,西西《開麥拉眼》在1964年8月1日首刊,《四方談》在1964年9月5日首刊。
[62] 轉引自馬鴻述、陳振名編著:《香港華僑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58),頁114。
[63] 「新趣」版《十三妹專欄》〈從更正扯起〉,1963年8月4日。
[64] 《星島晚報》「港聞」版1957年4月1日:「有的教科書,取材既不高明,連文句也不通。用白話寫的,完全不是『國語』,讀起來,使人忍不住發笑。」轉引自馬鴻述、陳振名編著:《香港華僑教育》頁142。
[65] 陳平原:〈學術文的研習與追摹——「現代中國學術」開場白〉,《雲夢學刊》,第28卷第1期(2007年1月),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