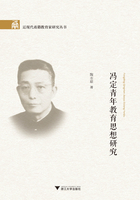
第四节 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如果说冯定在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求学过程中,主要的任务是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从而成为有文化的人,附带收获是结识的部分校友后来成了自己在革命道路上的亲密战友,那么冯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则完全是为了革命的历史使命而提升自己的革命修养,所结识的校友基本上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一、为保存革命力量成为派送的留苏人员之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定赴武汉,顺利接上组织关系,先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宣传干事,后接中央军委的通知,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训练股长。在此期间,冯定曾作为上海代表出席第五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
“宁汉合流”后开始的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的行为,使共产党员在武汉都待不下去了。当时,张太雷安排了一批非武汉的共产党干部即所谓的“下江人”在武汉开展革命工作,但他们说话的口音都不对,很容易暴露,张太雷就安排把这些口音不对的干部全部迁离武汉,冯定就是其中之一。冯定按照组织的意见携介绍信返回上海。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革命遭到残酷镇压,国内处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有计划地把一些在革命时期有一定影响的同志送往苏联学习。冯定经过陈修良的再三动员,打了要求去苏联学习的报告,并由陈修良转交给党组织审批,随后申请获得批准。
1927年10月9日,中国工人代表团秘密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陈修良当时是小组长,带了一批人假扮民工,从上海的吴淞口乘上苏联的一艘商船(苏联客轮“安铁捷号”),就这样从上海混出去了。商船一直把他们运到海参崴,然后代表团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抵达了莫斯科市。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向忠华,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李震瀛、邢经珠、冯定、胡任生、沙文汉、陈修良等60余人。由上海同船赴苏联的还有上海、武汉、江苏、浙江等地的中共干部共40余人。中国工人代表团共有100多人,分为5个小组,陈修良是小组长之一。1927年11月,中国工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冯定与大部分同志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第三期学员。这期学员中还有铁瑛(女)、章汉夫、帅孟奇(女)、陈徵(沙可夫)、陈铁真(孔原)、应修人、陈昌浩、陈逸(陈修良)(女)、陈尚友(陈伯达)、孟庆树(女)等。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还有杨尚昆、伍修权、孙冶方、张崇德、张崇文等。
那么,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由苏联出资创办的中国学校,该校曾培养出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蒋经国等一批两大政党的重要人物。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就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俄文全称是“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孙中山在1925年3月逝世后,苏联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苏共领导集团很快做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除武器支援外,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为旗帜,招来大批中国先进青年。其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并使其成为今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1928年年初,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二、遭遇莫名其妙的“苏浙同乡会”事件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江苏人、浙江人因为吃不惯当地面包,所以喜欢大家聚一聚、吃吃饭。当时大家也都没有什么钱,但有几个资格老些的学生,像孙冶方、蒋经国等,他们已经来了好几年了,靠做翻译赚了点工资,大家就敲他们的竹杠,要求他们请大家吃饭。老资格的学生就拿钱出来,请大家吃一顿饭,这是很正常的聚餐活动。
当时正好有一个人叫王长熙,从那里走过看到大家在里面聚会,他一看,多数都是苏浙人,虽然也有贵州等别的地方的人,但管他呢,反正可以借此“一网打尽”了。于是他就去报告王明等人说“他们那里在搞苏浙同乡会,在搞小集团,在搞宗派主义,闹得沸沸扬扬,可不得了”。向忠发(当时是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让这些参加聚餐的学生一律坦白,并追查“苏浙同乡会”的事情,威胁说如果不供出来这个事情就是反革命,就要被枪毙。当时的陈修良年纪很轻,听了十分害怕,怎么会这样呢,她真的想不通。
三、支部派卷起的迫害风潮
当时王明那派就是所谓的支部派,已经搞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最开始的支部派里面又分作两派,一派是教务派,一派是支部派。支部派就是支部高于一切。莫斯科中山大学里有很多教务派的人,所谓教务派的人都是中共原来最老的一批人,比如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孙冶方等,这些人都不是王明那一派的。
当时,米夫副校长支持王明等人,控制了学校支部内的领导,他们召开了有名的“十天大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多数中国同学。他们诬蔑原支部的领导人俞秀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书记)等同志是所谓“苏浙同乡会”等反革命组织的人,实行清党,把许多同志开除出党,甚至将他们逮捕后流放到西伯利亚,使不少同志牺牲在苏联。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米夫派于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却一致肯定米夫派、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及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处分,有些人自杀了,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在这场运动中,冯定也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不赞成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观点,遭到了批判,被列入反支部派。当时批判他的理由非常特别,说他没有认真看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书,只是对孙中山的著作有兴趣。但由于冯定出生于手工业家庭,所以他只是受到了警告处分,并于1930年3月被下放到莫斯科第七印刷厂劳动。除冯定之外,被下放到工厂去的同志还有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张崇文等,冯定与张崇文被分配去学习放纸劳动,其他同志是叠报纸。冯定聪明好学,对劳动充满了热情,因此很快就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放纸技能,直至1930年被遣送回国。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为什么总是如此坎坷不平?一些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为什么会遭受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打击?这场斗争迫使冯定专心致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中寻找答案。
所幸,冯定虽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因抵制党内王明等人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而遭受了排斥和打击,但他在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并未沾染上教条主义思想,而是把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铭记终生。冯定把思考人生和从事教育的志向相结合,为回国后将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提升到理论高度,为与青年平等对话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