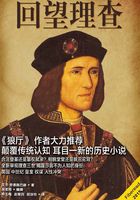
第10章 1619——宫廷庆典主事(2)
总而言之,略过莫尔的戏剧风格,对比他著作里的推测和大部分资料显示的事实,一个全然不同,不为人知的理查呈现了:他形象良好,正当继位,能力出众。和莎士比亚戏剧的主角完全相反。那究竟发生了什么?托马斯·莫尔把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写成是撒谎成性的阴谋家。看似真诚善良,实则虚情假意,篡位之心由来已久。我的著作《关于理查三世生平与统治的历史》会说明,这一切只是空穴来风。但是,莫尔正是借助对“虚情假意”的描写暗示其书中主角(理查)的狼子野心,他炉火纯青的讥讽手法使人物活灵活现。我相信,这讥讽也正是莎士比亚大师戏剧人物(理查)的灵感来源。
请您打消格洛斯特公爵理查言行不一,一直觊觎王位的看法。事实保持不变,但是含义截然不同。它们呈现出国王真正的形象:私下温和谦逊,当众则英明善断,对同盟慷慨,对敌人仁慈。通过在国家中部建立政府根据地,理查加强了法制改革,这在北方早已实行。证据不胜枚举!
您难道宁愿对此充耳不闻吗?我知道您的家族时而深受伊丽莎白一世——我们伟大的都铎女王的宠信,时而遭遇冷落。但是我也知道,您信奉真理,明白好心也可能被当成驴肝肺。任何人都可能有此困境。理查三世可能犯下的较轻罪行——处死老朋友黑斯廷斯,一直被夸大其词。但是其他统治者却被区别对待。比如亨利·都铎,消除了无数异己。如果他都不算罪大恶极,那为何理查要受此污名?
在博斯沃思之战后,胜利方都铎王朝数年内暴乱频发,反映了约克家族深得民心。亨利七世是因为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爱德华四世的女儿,才被接纳为新朝代的创建者。得人心的是她,而不是他。他们孕育了四个孩子,包括后来的亨利八世,他是举世无双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现在是1619年,我们生活在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一世国王的庇荫下。我们可以不必顾虑抗拒事实的都铎时期。被迫要哗众取宠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如果我们有让人信服的论据,还能修正官方说法。历史是作用与反作用的连锁反应。偶尔我们会在事发已久后出乎意料地瞥见一丝公正,从而促成几代人之间私生活的和解,理顺造就历史的大事件。犯罪者可以变成受害者,统治者可以变成流亡者。您的家族不止一次发现,人们总被多方摧残。但局势总会扭转。诽谤和污蔑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失。
我的家人可能随时会回来,满载黑莓而归。但是我想借此机会问问您,前些年我们对此问题一直意见相左。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歌或小说比历史更为严肃和重要。但前提是这些诗歌或小说已经变成事实。莎士比亚大师是故意言过其实,还是因为他很守旧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篡改了事实?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他的讽刺手法和他的艺术责任能否平衡?他何出此举?是投机取巧还是另有政治目的?
大人,当我追寻到问题的关键时——我开始相信关键就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我气馁了。我突然有预感,这封信会尘封于您陈列室里华丽精致的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但是我不应该被恐惧控制,绝不应该。我应该对您的良好判断、渊博学识以及正义感有信心,这是我作为下属应该做的。所以我继续欣喜若狂地执笔,因为下午快要过去了。
我第一次看到莎士比亚大师的戏剧《理查三世的悲剧》,就印象深刻。我最近才从加的斯回来,行李都未收拾,就奋笔疾书了。剧中描述的恶魔阴森可怕,前所未有。剧作家多么大胆,创造了具有毁灭势力的权利象征!容许我详细描述剧中诡计多端和挑拨离间的暴君:他无所顾忌地和命运比赛,他花言巧语蛊惑人心,即使情况有变,他也能加以利用,这种能耐真是神憎鬼厌。在剧中,只有女人敢于对抗他的淫威。
我的活动宣传小册鼓舞人心,深受好评,因此我就在河边筹办活动,先是十二月庆典,接着是主显节盛宴[8]、宫廷表演以及复活节庆祝胜利的游行。作为新戏的审查官,我可以充分利用我的外交技能。在和表演公司以及剧作家的协商中我研究了许多戏剧。履行作为皇宫庆典主事的职责,我乐在其中。我一直都观看《理查三世的悲剧》的新演出。渐渐地我觉得,这是老式悲剧的巅峰之作——主角都曾是命运的宠儿,最终却落得英年早逝的下场。在莎士比亚大师后期的戏剧中,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是由人物主导的,人生重大问题也被小心谨慎地融入了矛盾冲突之中。
起初阅读托马斯·莫尔的《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让我其乐无穷。我清楚了莎士比亚是如何受惠于这本书,他又是多么巧妙地把它改编为戏剧。但研究我们先辈的生平时,我发现了一些我之前从不知道的事情。真正的理查三世让我烦躁不安。我越了解事情的经过,就对这戏剧越生厌。莱格的拉丁语戏剧《理查三世》[9]及《理查三世的真正悲剧》都大受欢迎,但是莎士比亚戏剧更功成名就,经久不衰。看着《理查三世的悲剧》是多么灵活自如地迎合人类对轰动事物和含沙射影的嗜好,我由欣赏变为愤怒。我发现,它集艺术,讽刺手法和政治宣传于一身,多么可疑的结合。任何普通的纽盖特监狱犯人都可以成为作品主角的原型。戏剧导演总是遍读古老编年史和书籍,内容尽是毫不相关的传闻,从中搜寻异常邪恶或英勇之士生平所做的阴险之事。
写作《关于理查三世生平与统治的历史》时,我踩在了历史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历史是事实的收录(比如沃尔特·罗利船长去年被处决的残酷事实),另一方面历史是都铎王朝关于暴君的传唱已久的民谣。理查三世是否谋害了他的侄子?您会在我的书中以及信里找到真相。就是我设法维护的真相。民谣的拥护者会说世上没有真相。所有事情都分帮结派,那么历史可以给予我们什么教益?而且,戏剧还创造自己的世界!确实如此。很多事情历史研究做不到,但是文学和戏剧可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探讨人类的黑暗面,莎士比亚剧中主角的大起大落——即刻起我应该将此主角称为都铎理查[10]——会比事实更有导向性。虽然戏剧声称会反映“真相”,但只是关于正派与反派的肤浅真相,它实际上模糊了事情的真正过程。
大人,戏剧可以让我们受益良多,但是它无法告知我们历史。了解了所有事实后,我看到了英格兰王国的分歧,一道大大的裂缝。一边是人们噤若寒蝉,另一边却是老调重弹。我相信,我们不仅能享受艺术之美,还能吸取前车之鉴。但是,理查三世的故事却蛛网尘封,很多事实都被忽略,要不就完全被歪曲。要是我们意识到历史和这部戏剧是一体两面该多好。但是民谣传唱了一个世纪之久,流传下来的只有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国王——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他在博斯沃思的战败被描述为邪不胜正,反映了错误的推理,胜利方正是以此歪理在历史画卷中为自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宣扬是上帝赐予了他们胜利,因此他们的大业是顺应天意的,敌人是罪大恶极的。噢,您肯定知道这种惯用伎俩。
莎士比亚从都铎时期的作家中寻找灵感,运用他的戏剧来说明上帝的安排:骄兵必败。上帝的对手、体现邪恶的角色,最后都会遭受惩罚。考虑到关于理查畸形的离奇故事,似乎这样才相称。混杂了傲慢,堕落,欺骗,遮掩,诱惑等等,就这样,一个蛊惑人心的恶魔现形了,和他的观众,也就是我们,共享成功。
您会问,为什么都铎理查会被上帝惩罚?当然是因为他违抗了上帝神圣的命令!但这些罪行只是有人为了牟取私利而捏造的。我头脑冷静,此外还是个新教徒。如果上帝真想摧毁金雀花王朝,让新王朝取而代之,那么理查的行为,不管好坏,都无关痛痒。认为上帝的角色是定夺我们的因果报应,是多么狭隘!
起初这种道德把戏并不明显,传统也还未成型。托马斯·莫尔创作书中场景时一定喜不自胜,带着知识分子的傲慢,这种傲慢是受到了约翰·莫顿的熏陶。您请记住,莫尔十一岁就被送到红衣主教的家里学习礼节。这算是一流教育,他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名门大家。但是约翰·莫顿是谁?我们都知道的,他是亨利·都铎的左膀右臂,是利用歪理压榨人们的幕后黑手。莫顿争辩说,倒不如穷人缴税,这样富人就可以少缴许多——有何不可呢?
大人,一百年后每个人都还记得莫顿的胡话,但没人意识到这个红衣主教曾经是伊利主教,是对理查最怀恨在心的敌人之一。
在莎士比亚的舞台剧里,他是个无关紧要,毫无恶意的角色。想想戏剧大约进行到一半时伦敦塔里的草莓那一幕。都铎理查情绪高昂地走进会议厅,问伊利主教,也就是莫顿,要一筐他花园里的草莓。等草莓送来后,理查的兴致却完全改变了,转而砍了老朋友黑斯廷斯的头。理查恣意肆虐的暴君形象让人难以忘记。莎士比亚大师直接从托马斯·莫尔的书中抄袭了这个场景。我猜测,莫尔肯定亲眼看过他花园里的草莓。要不是和红衣主教熟识,他何以得知如此琐碎之事?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年幼的男孩莫尔在主人莫顿家接受教导,主人在漫步花园时顺便告诉他草莓地的事。又或者是这样:红衣主教莫顿——后来的坎特布雷大主教——坐在篝火旁,讲述过去发生的奇闻轶事,年幼的酒童莫尔被逗得大笑,并重新给主教倒满波尔多葡萄酒。
草莓那一幕非常引人瞩目,可能这对莎士比亚大师来说是最重要的。在戏剧中,素材一定是为戏剧张力服务的。实际上,从他与托马斯·莫尔的两点主要偏差中可以看到“剧作家之手”。
首先,莎士比亚大师并没有赋予都铎理查任何目的感。因此理查没有动机做出恶行。尽管他挑拨离间,对权力游戏乐此不疲,但是这个角色并不丰满。他缺乏理性,明显是凭想象力虚构的人物。他的目标变来变去,朝三暮四,为了谋权篡位而逢场作戏。综合起来,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傲自大,违抗天威的人物形象。他孤注一掷和上帝斗争,这是赋予莎士比亚作品普遍意义的主题。《理查三世的悲剧》尽显主角的傲慢无礼,狂妄自大。这是一个过于高估自己的人,以为自己可以藐视法律与天道。
其次,莎士比亚大师小心翼翼地为理查走向毁灭的下场埋下伏笔。此作品和他的其他三个历史剧息息相关,它们是关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的冗长战争。战争冲突是由玛格丽特女王引发的,她是兰开斯特家族背后的推动力量,以失败告终。虽然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继位时她已经在法国去世,但是在莎士比亚的剧中她不但活生生的,还一心想着复仇。受她预言的指引,观众可以看到上帝所起的作用。此剧深受罗马剧作家塞内加[11]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的剧作家远不止于此。玛格丽特女王反复哭喊,悲痛欲绝,满腔复仇怨恨,把这部剧变得像驱魔仪式。女性角色充当合唱团,代表无能的英格兰。当她们效仿特洛伊女人,唱起耶利米哀歌[12]时(两者都有相似的不祥之兆,伴随着一个人的出生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剧情呈现出冥冥中一定是有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这个类比没有解释的余地。“充满绝望和死亡气息”的合唱强调一个丧失救赎权利的人将受到万劫不复的惩罚。这样,莎士比亚勾勒了一个关于诅咒的神学概念,这是托马斯莫尔从未提及的。
剧作家莎士比亚意识到他夸大事实了吗?我认为是的,大人。他的意识就像树一样滋长,虽然缓慢但是无法阻挡。我热爱舞台戏剧,尤其是莎士比亚大师的作品。可我对它们却疑惑不解。此部艺术作品中的暗示和史实完全不符。几乎所有事情都被颠倒了。但是艺术视野占据了上风。
剧作家们都重新解释历史事件,莎士比亚大师更是无所顾忌地歪曲事实,他在之后的作品中也是如此,比如《麦克白》[13]。所以为什么我把这部关于理查三世的戏剧看作诽谤?为什么它的每次新演出都犹如千斤重担,使我良心不安?
都铎理查是一个吸人眼球的角色。但是,是托马斯·莫尔对历史了解不足,才会把他塑造成反复无常的形象。剧作家莎士比亚纯粹地使用一贯的讽刺手法,追求政治私利。他需要做的只是插入一些文学手法和随意参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14]来完成他骇人的“普遍的”暴政象征。
终于,我听到树林里传来我妻子和女儿的声音,萦绕身后,响彻山丘。她们要回来了,我的心情也变得愉悦。很快厨房就会变得熙熙攘攘,她们会在里面完成各种工序:对黑莓进行筛选、清洗、煮沸以及保存。我女儿的双手会被染得蓝蓝的。那时我妻子又会埋头刺绣。她从来不和我倾诉衷肠,也不会从后面偷看我在写什么。我对此早已习惯。我的家人完全不了解我对理查三世的热爱、我研究的内容以及我担心的事情。他们为何要了解呢?我的妻子把我忙于看书和写作当做是自然法则。她会帮我清洗钢笔,但是不会提出任何问题。她以我为荣吗?她不会知道我哪里让她引以为荣,我也不会责怪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