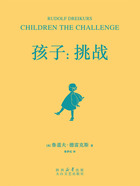
第四章
孩子的错误目标
妈妈正在写信。三岁的乔伊丝在旁边的地板上玩玩具。她突然跳起来跑向妈妈,要求拥抱。妈妈回应道:“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娃娃放到马车上,带它出去兜兜风呢?”“我想要你陪我玩。”“过一会儿再玩,乔伊丝。我得先把这封信写完。”孩子慢慢地退回去,继续玩她的游戏。几分钟后,她问:“妈妈,现在可以玩了吗?”“还不行,亲爱的。”妈妈心不在焉地回答。安静了几分钟后,她说:“妈妈,我要去洗手间。”“好的,乔伊丝,去吧。”“但是我的连体衣脱不下来。”“你可以的,”妈妈抬起头来说,“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乔伊丝漫不经心地尝试了几次,没能把衣服脱下来。“好吧,亲爱的,快过来,这回我帮你脱。”乔伊丝离开了房间,妈妈继续写信。不一会儿,女孩又回来了,需要妈妈帮她把连体衣穿上。妈妈又帮了忙,然后继续写那封信。安静了几分钟后,乔伊丝又问:“现在可以陪我玩了吗?”“再过几分钟,亲爱的。”很快乔伊丝又来到母亲身边,抱住她的膝盖说:“我爱你,妈妈。”“我也爱你。”妈妈一边说一边拥抱了女儿。乔伊丝回去玩玩具了。妈妈写完信,就开始和乔伊丝一起玩。
这个故事似乎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耐心、慈爱的母亲和她与孩子之间的良好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写在这里呢?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妈妈与孩子的互动。乔伊丝在做什么呢?她在用一种可爱又迷人的方式持续索要关注。她的行为其实是在说:“除非你注意到我,否则我就什么都不是。只有当你围着我转时,我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孩子们总是迫切地想要获得归属感。如果一切顺利,孩子的勇气得以维持,他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他会去做符合形势的事情,并通过参与其中和发挥作用而获得归属感。但如果他是一个受挫的孩子,他的归属感就很有限了。他对参与集体活动的兴趣将转移到在他人身上获得自我实现这一孤注一掷的尝试中。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将转向这个目标,无论是通过讨人喜欢的或是令人讨厌的行为。无论如何,他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去追寻四种公认的错误目标。如果我们希望重新引导孩子采取一些建设性的方式来融入社会,就必须对这些错误目标有所了解。
渴望得到过度关注是受挫的孩子用来获得归属感的第一个错误目标。他会错误地认为,只有当他成为他人注意力的中心时,他才有存在的意义。受这种错误假设的影响,孩子会逐渐发展出一套获取他人注意力的有效机制。他总能找到各种方法让他人为自己忙得团团转。他可能表现得迷人而聪慧,可爱又腼腆。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的讨人喜欢,但他的目标其实是赢得关注,而不是真正地参与。
在上面的事例中,乔伊丝看起来是想要参与,她想让妈妈和她一起玩。那么我们是如何确定乔伊丝出现了不良行为呢?这很简单。参与意味着配合形势的需要,做出合作的行为。勇敢自信的孩子会感觉到妈妈除了和她一起玩之外,还需要做别的事情。乔伊丝则有不同的想法。她觉得如果妈妈在忙别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忘了。乔伊丝认为,只有获得关注,她才能确立自己的位置。
讨人喜欢的关注获取法一旦失败,孩子就会转向令人讨厌的方法。他可能会哭哭啼啼,磨磨蹭蹭,用蜡笔在墙上涂鸦,把牛奶洒出来,或者尝试另外一千种获取关注的方法。至少当爸爸妈妈对他大发脾气的时候,他能确信他们知道他的存在!这样的孩子已经产生了错误的自我认知。我们每一次屈服于他对过度关注的要求时,就是在强化他错误的自我认知,并使他更加坚信,这种错误的方法能帮助他获得自己所渴望的归属感。
当然,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注。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训练、同情与爱。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己,发现我们只不过是在孩子想要获得持续的过度关注时被迫地给予,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当肯定,这就是孩子想要我们做的,这也是孩子为了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采取的错误方式。
乍看之下,我们似乎很难将适度关注和过度关注区分开来。秘诀就在于区分孩子是否能够认识到整体形势的需要。参与和合作要求家庭中每个人都以形势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父母可以在心理上退后一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孩子的行为和反应似乎是高于形势所需的——正如乔伊丝的故事所示——那么孩子有可能正在要求过度的关注。通常,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反应来确定孩子无意识层面的意图。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也会发生在无意识的层面,我们只是在“自然地”顺从孩子的安排。当我们意识到这种互动并逐渐有能力对其进行解读时,我们就把它带到了意识层面,从而获得了为孩子纠正错误或提供指导的方法。
五岁的佩吉正在看电视。妈妈已经第三次提醒她该睡觉了。每次妈妈提醒她的时候,佩吉都哭哭啼啼地恳求,想过会儿再去睡觉,至少把“这个节目”看完。妈妈让步了,因为这确实是个好节目。然而,当节目结束时,妈妈再次提醒佩吉上床睡觉,这回佩吉完全不理妈妈,换了个台继续看电视。妈妈走进房间:“佩吉,你早该睡觉了。好了,现在做个好孩子,上床睡觉去吧。”“不!”佩吉回答。妈妈俯身对她生气地说:“我说了让你上床睡觉。快去!”“可是,妈妈,我要看……”“你要我打你屁股吗?”妈妈打断佩吉,关掉了电视机。佩吉立刻尖叫起来:“你这个刻薄的老东西!”她冲到电视机前,想把它重新打开。妈妈抓住佩吉的手,打了她一巴掌,强行把她拉出了房间。“够了,这位小姐。现在你该上床睡觉了。快,把衣服脱了。”佩吉尖叫着反抗,脸朝下扑倒在床上。妈妈有些颤抖地离开了房间。二十分钟后,妈妈回来看看情况如何,发现佩吉还穿着衣服,正在看一本书。妈妈气坏了,打了佩吉的屁股,给她脱掉衣服盖上被子。
首先,佩吉很清楚自己的睡觉时间到了。但如果她磨磨蹭蹭,要求多看一会儿电视,她或许能挑战妈妈的权威。因此,当妈妈让步,让佩吉再看一会儿时,就正中了女儿的下怀。佩吉的行为似乎在说:“让你照我说的做,就能显得我很重要。”当她哄骗着妈妈让自己再多看一会儿电视时,妈妈照她说的做了。于是她成功地展示了自己战胜妈妈的能力。
由此可见,对权力的争夺是第二个错误目标,这通常发生在父母试图强行阻止孩子对关注的要求一段时间之后。从那以后,孩子就下定决心要用权力来打败父母。他拒绝做父母想让他做的事情,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这样的孩子会认为,如果自己服从别人的要求,就相当于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力量,从而失去个人价值。这种对于被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所压倒的恐惧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现实,会导致他们做出一些可怕的努力来展示自己的力量。
当佩吉的妈妈坚持要佩吉在看完电视节目后上床睡觉时,妈妈和佩吉就陷入了一场权力竞赛。故事的其余部分说明了一个人是如何试图证明自己才是老大的。每次妈妈心烦意乱,打佩吉耳光或打她屁股时,都把胜利拱手让给了佩吉。受惩罚的侮辱和痛苦是为了获胜而付出的代价:让妈妈心烦意乱并最终宣告失败——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在感到彻底失败或脾气失控时会做的事情。我们的行为其实是在说:“除了体形和力量的优势,我什么也不是。”孩子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并利用它。你难道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把父母弄得恼羞成怒、歇斯底里时,内心是如何窃喜(尽管表现出来的是眼泪和尖叫)的吗?
试图用权力去压制一个沉溺于权力的孩子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也是徒劳的。在随之而来的长期斗争中,孩子只会越来越善于使用自己的权力,并且更为根深蒂固地相信,除非自己展现出无上的权力,否则就一无是处。这样的成长可能会把孩子推到一种危险的境地,他会发现唯有当一个恶霸、一个暴君才能让自己满足。
权力竞争的问题之所以在当今社会变得如此普遍,是因为我们的平等观发生了变化。我们将在第十六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就目前而言,只要能够认识到,当父母和孩子都试图向对方展示谁是老大时,就存在着权力之争。
要求关注和展现权力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孩子在被纠正后的行为。如果他只是想引起关注,在被纠正后他通常会停止令人讨厌的行为,至少在被骂的时候会停下来。但如果他的意图是展现权力,那么试图让他停下只会加剧令人讨厌的行为。乔伊丝和佩吉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区别。
妈妈在厨房,爸爸在地下室。五岁的罗伊和三岁的艾伦在客厅里玩。突然,艾伦痛苦地尖叫起来。爸爸妈妈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艾伦蜷缩在角落里尖叫,而罗伊竟用一个点着的打火机在烧弟弟的胳膊。爸爸妈妈赶到时伤害已经造成,罗伊成功地把艾伦烧得很惨。
第三个错误目标源于权力竞争的加剧。当父母和孩子越来越深地卷入权力斗争,每一方都试图制服另一方时,就有可能演化成一场激烈的报复。孩子在受挫时可能会寻求报复,以此作为他获取重要性的唯一途径。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确信自己不讨人喜欢,也没有任何权力,只有当他能像别人伤害自己一样去伤害别人时,他才觉得自己重要。于是他的错误目标变成了反击和报复。罗伊在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时极度受挫,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没人喜欢的坏孩子。正因他的行为是如此令人讨厌,他也成功地让自己“坏孩子”的形象深入人心。这样的孩子是最需要鼓励的,却往往最缺乏鼓励。需要有人能真正理解与接受孩子的本来面目,来帮助他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如果爸爸妈妈惩罚罗伊的话,只会进一步证明他的“坏”。这也会进一步地激怒他,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报复与相互伤害。
第四个错误目标出现在完全受挫的孩子身上。他们试图证明自己一无是处。
八岁的杰伊在学校遇到了困难。在一次家长会上,老师告诉妈妈,杰伊的阅读能力非常差,所有科目都很落后。无论他多么努力,无论老师给他多少额外的帮助,他似乎怎么也学不好。“杰伊在家会做什么家务吗?”老师问。“我不再让他做家务了,”妈妈答道,“他什么也不想做。即便他想做,也总是冒冒失失的,做得很糟糕,所以我再也不要求他做家务了。”
一个完全受挫的孩子会彻底放弃:他觉得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成功的机会,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他变得很无助,并学会了利用这种无助,夸大自己身上任何一个真实或想象的弱点或缺陷,以逃避一切任务,因为他觉得自己肯定会失败,而失败会使自己更难堪。一个看似愚蠢的孩子往往是一个受挫的孩子,他们把愚蠢作为逃避一切努力的一种手段。这些孩子仿佛在说:“任何事情如果我去做了,你就会发现我是多么的没用,所以别来烦我。”这些孩子不再为别人做任何事情。他们彻底放弃了。每当妈妈发现自己在说“我放弃!叫他做什么都没用”时,她可以明确地知道,这正是孩子想让她感受到的。孩子仿佛在说:“放弃吧,妈妈。没用的,我一无是处,毫无希望。别管我了。”当然,孩子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是一次又一次面对不可能克服的障碍所带来的错误认知。他极度受挫。事实上没有一个孩子是一无是处的!
当我们意识到孩子的错误行为背后可能存在这四个错误目标时,我们就有了行动的基准。对孩子进行让他产生错误目标的恶意揣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好处的,甚至有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心理学知识应被用来作为我们行动的基准,而不是攻击孩子的武器。孩子对自己的真实目的一无所知。我们可以使一个孩子意识到他的真实目的,但这种披露行为应该留给专业人士。然而,一旦意识到孩子的错误目标,我们就能意识到他行为的真实目的。原本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现在开始变得有意义了,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了。如果我们避免了孩子想要的结果,那么他的某些行为就会变得无效。如果孩子没有达到目的,那么他就有可能重新考虑方向,选择另外一种行事方式。
当意识到孩子在要求过度关注时,我们可以避免屈服于他的要求。如果妈妈不在身边,要求关注还有什么意义呢?当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权力竞赛时,我们可以退出战场,不让自己卷入这场竞赛。在空无一人的赛场中成为胜利者是毫无意义的。当一个孩子试图伤害我们时,我们要意识到他内心深处其实是受挫的,不要去伤害孩子的感情,不要用惩罚的手段来报复孩子。我们还可以停止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孩子感到遗憾,可以安排一些活动来帮助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如果妈妈并不相信自己是无可救药的,那么放弃又有什么用呢?
随后的章节将用实例来展示这四个错误目标,并描述使它们失效的可行方法。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即这四个错误目标只常见于幼儿。在成长的早期,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发展自己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关系上。他把自己看作成人世界里的一个孩子。在这一时期,这四个错误目标对知情的观察者来说是相当明显的。然而,当孩子长到十一岁左右,他与同伴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他开始追求更广泛的行为模式,以在同伴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出于这一原因,令人不安的行为(通常是孩子寻找自己位置的错误努力)不再能完全用以上四个错误目标中的某一个来解释了。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挑衅行为有时也可以用这四个错误目标来解释,但同时也存在其他的错误目标,例如寻求刺激、过度关注男性特质、执着于物质成功等,这些不一定在上文提及的四个错误目标里。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必须铭记于心——我们作为父母,所能做的只有试着去激励孩子做出行为上的改变。即使我们做对了事情,也不一定总是成功。(无论如何,期望自己事事成功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每个孩子都是自己所作所为的决策者。家庭以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同龄人的影响,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发现把孩子引向另一个方向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就必须要记住,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和决定。我们不能对此负责。选择权和决定权永远属于孩子。而这,也正是平等的一部分。
生活是由无数个时刻组成的,如果我们在这一时刻做出了正确的事情,就会进步。另外,如果我们不能满足特定情况的要求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么进步的机会确实是渺茫的。
当然,我们的问题不可能总是立即得到解决。这一时刻只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这些事件要么带来解决方案,要么造成延迟,要么使事情无法解决。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这些时刻要么有助于训练,要么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要么正好相反——培养有害的态度与不良的社会关系。
孩子们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一步一步来解决。在这本书中,我们试图指出,在特定的冲突情况下,哪些步骤可能是有益的,哪些可能是有害的。对大多数父母来说,在多数情况下,能够明确在特定情况下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就已经足够了。在过去,这些知识对所有母亲来说都是常识,也就是所谓代代相传的育儿传统。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如今的民主环境中,澄清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育儿观念。
在许多案例中,孩子错误行为背后的错误想法和错误目标是如此根深蒂固,可能需要不止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父母可能需要努力重新构建一个孩子的基本假设与个性模式,需要对他的行为动机进行更全面的洞察。在必要情况下,父母可能会发现参加家长学习小组、参加心理咨询中心的活动,或接受一对一咨询是有帮助的。学习更多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理论书籍也是必要的。
我们希望提供对一些日常操作的解释——为那些忧心忡忡的母亲提供一些帮助,她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拥有影响孩子的巨大潜力,前提是她明白该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父母越是能够真正地了解他们的孩子,就越是能够帮助他们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以更为具象的图景为目标去生活,接受和谐合作所必需的社会价值观,并最终在生活中实现真正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