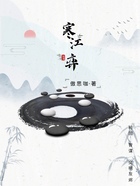
第4章 药藏锋
太医院东厢房的药柜泛着陈年柏木香,裴照雪指尖抚过“乙未”字号抽屉的铜环,环上挂着的朱砂绳结褪成了褐红色。药童踮脚举着油灯,灯油滴在青砖地上凝成个蜡泪圈,圈心粘着半粒黍米——尚膳监昨夜送药膳时落下的。
“取三钱白矾,要去年霜降前晒的。”裴照雪敲了敲药柜第三层,抽屉底板发出空响,像是夹层藏着什么。药童的灯笼裤膝盖处磨得透亮,爬梯子时露出截靛蓝袜腰,针脚细密得能筛米——尚服局绣娘的活计,却穿在个粗使药童身上。
廊下忽传来阵窸窣声,陆九川蹲在滴水檐上啃芝麻糖,怀里揣着刚摸来的尚药局钥匙。糖渣掉进晾晒的当归堆里,引得只花斑猫蹿上药架,爪子勾破张防风宣纸。裴照雪银针脱手钉住纸角,纸面墨迹未干的《千金方》补遗页上,赫然多出个猫爪印的“七”字。
药童捧来的白矾块裹着层黄纸,纸缘印着户部的鱼鳞纹暗记。裴照雪碾碎半块矾石,粉末在晨光里泛着诡异的靛蓝色——这分明是浸过硫磺泉的辽东矾。花斑猫突然炸毛蹿向院墙,撞翻晾晒的枸杞筐,红果子滚到陆九川脚边,被他顺手塞进裤袋三颗。
“先生,院判大人有请。”小太监的云履底沾着朱砂,在青砖上踩出朵歪扭的莲花。裴照雪袖中银针在矾粉上一蘸,针尖顿时蒙上层幽蓝。陆九川在檐上猛打喷嚏,芝麻糖碎喷进药柜缝隙,正卡在“乙未”抽屉的锁眼里。
院判值房飘着龙涎香,博古架上的钧窑药瓶缺了个耳,瓶身冰裂纹里渗着褐渍。裴照雪跪坐在蒲团上,盯着案头那方端砚——墨条磨出的浆水泛着绿光,分明掺了铜锈。院判的麒麟补子前襟沾着星点白霜,细看却是碾碎了的砒霜末。
“裴先生看看这方子。”院判推过张洒金笺,户部的朱砂印被茶水晕成团红云。“九皇子举荐的游医里,唯有你活过了三日。”院判的翡翠扳指叩在案上,青筋暴起的手背压住张泛黄文书——正是伪造的幽州知州医案副本。
陆九川从窗缝瞅见洒金笺,袖中羊皮食单滑落半截,腊月初八的辽东参记录被风掀开,墨迹圈着的“乙未”二字正对药柜方向。
药童突然捧着药盅闯进来,盅底结着层蓝沫,与慈宁宫那碗毒药如出一辙。裴照雪银针在盅沿刮了道白痕,针尖霎时发黑:“大人这盅子,倒是像都察院上个月失窃的贡品。”药童的靛蓝袜腰忽地滑落半寸,脚踝处靛青刺青清晰可见——正是周珩暗卫营独有的“九曲蛇纹”,暗示其双重间谍身份。
罐里滚出颗蜡丸,遇热化开半截,露出里头焦黑的辽东参须。陆九川的芝麻糖棍“啪嗒”折断,糖块正砸在药童后颈,少年一个激灵撞向药柜,“乙未”抽屉“哐当”弹开半寸。裴照雪袖风扫过案头,洒金笺飘进炭盆,腾起的火苗里显出个盐引状的焦痕。
院判的乌纱帽翅颤如蝶翼,靴尖悄悄勾向博古架下的机关。裴照雪突然剧烈咳嗽,帕子上的“血迹”甩到麒麟补子上,茜草汁遇砒霜末“滋啦”冒起白烟。陆九川趁机翻窗而入,裤袋里的枸杞撒了一路,花斑猫追着红果窜上房梁,震落积年的陈灰。
“好个声东击西!”院判的机关踏板被枸杞卡住,博古架缓缓移开,露出墙洞里的靛蓝布匹。裴照雪银针挑开布角,里头裹着的黄符纸朱砂未干,背面盖着都察院的獬豸暗印。药童的靛蓝袜腰突然崩线,露出脚踝处靛青刺青——麻绳状的“七”字。
陆九川的羊皮食单被猫爪撕破,腊月初八的记录缺了半角,残页上“十五斤”的“五”字少了一横。院判突然暴起,麒麟补子下摆扫翻炭盆,烧红的银霜炭引燃靛蓝布匹。裴照雪袖中银针连发三枚,钉住院判的环跳、曲池、膻中三穴,老头儿僵成个提线木偶。
花斑猫在梁上炸毛乱窜,撞翻个紫砂药壶,壶嘴喷出的硫磺水浇灭火苗。陆九川捡起半块蜡丸,对着日光瞧见里头蜷着条僵死的蛊虫——足节上沾着白矾末。裴照雪银针挑破蛊虫腹部,蜡衣碎片簌簌掉落:“辽东参裹蛊虫入药,九皇子送来的药材果然别有乾坤。”
药童瘫在墙角哆嗦,袜腰彻底脱落,脚背上赫然印着靛蓝的“乙未”字样。
“原来是个活账本。”裴照雪银针挑破药童袜腰,靛青丝线里缠着张盐引残片。院判的乌纱帽被火燎出个窟窿,露出里头暗藏的铜钥匙——匙齿形状与慈宁宫乙未柜锁眼严丝合缝。陆九川的裤袋漏了个洞,最后两颗枸杞滚进墙缝,正卡在机关齿轮间。
日头爬上院墙时,太医院飘起焦糊味。裴照雪拢着灰鼠裘退出值房,袖中银针串着三样东西:蜡丸里的蛊虫、盐引残片、铜钥匙。陆九川蹲在墙根啃芝麻糖,羊皮食单卷成筒插在后领,残页上的“乙未”被猫爪挠出个豁口,活像张咧开的嘴。
太医院东厢房的焦糊味混着硫磺气,熏得陆九川连打三个喷嚏。他蹲在墙根揉鼻子,裤袋漏出的枸杞早被花斑猫叼走,红果子在青砖上滚出条歪扭的线,直通院判值房后墙的暗门。裴照雪指尖银针在铜钥匙齿槽一刮,带出星点靛蓝漆屑——与慈宁宫乙未柜锁眼的漆色严丝合缝。
院判僵在太师椅上,麒麟补子的金线被火燎得卷边,露出底下暗绣的“天佑裴氏”。药童缩在博古架后啃指甲,脚背的“乙未”刺青蹭上墙灰,活像盖了层宣纸拓印。陆九川摸出半块芝麻糖塞进锁眼,糖渣遇热融化,暗门“吱呀”裂开条缝,腥气混着霉味扑面而来。
“好个药藏洞天。”裴照雪银针挑亮火折子,甬道石壁上渗着黄褐水渍,手指一蹭嗅到熟地黄芪的霉味。陆九川贴着墙根摸进去,靴底粘了坨软烂物,就着火光细看竟是团发黑的辽东参须,须尖沾着白霜似的砒霜末。
甬道尽头堆着二十来个靛蓝布包,布角印着户部的鱼鳞纹。裴照雪银针挑开布结,里头裹着的黄符纸哗啦啦散落,朱砂画的蚯蚓字连起来竟是张北疆舆图。陆九川的羊皮食单突然发烫,残页上的猫爪印“七”字遇热膨胀,正对应舆图上的废弃烽燧堡。
院判的鼾声忽然在甬道口响起,花斑猫叼着枸杞蹿过青砖,撞翻个紫砂药罐。裴照雪袖风扫灭火折子,银针贴着陆九川耳廓钉入石壁,针尾缠着根靛蓝丝线——药童袜腰的断线。暗门“砰”地闭合,陆九川后颈一凉,某块碎石擦着衣领飞过,在靛蓝布包上砸出个盐引状的凹痕。
“劳驾让让。”裴照雪突然揪住陆九川的后领往右一拽,三枚铁蒺藜“笃笃”钉进方才落脚处。石壁机关“咔嗒”转动,靛蓝布包堆里弹出个樟木匣,匣面冰裂纹中渗出褐液,遇空气“滋啦”腾起白烟。陆九川摸出芝麻糖棍去挑匣盖,糖棍瞬间蚀成焦黑。
裴照雪银针蘸了唾沫往匣缝一插,针尖遇褐液泛起靛蓝。药童的啜泣声忽远忽近,脚踝铁链拖地声混着硫磺味飘来。陆九川扯下半截衣摆裹手,猛地掀开匣盖——里头蜷着条僵死的百足虫,虫腹鼓胀如珠,细看竟是颗包着蜡衣的辽东参。
“好个虫吃参!”裴照雪银针刺破虫腹,蜡衣碎屑里裹着张盐引残片,朱砂批红处缺了半枚户部官印。陆九川的羊皮食单突然被穿堂风卷起,残页贴到石壁舆图上,腊月初八的“乙未”记录正对应烽燧堡位置的墨圈。
甬道深处传来铁链断裂声,药童光着左脚跌跌撞撞跑来,脚背的“乙未”刺青蹭出血痕。裴照雪银针连发三枚,钉住他破损的裤管,靛蓝袜腰彻底脱落,露出小腿肚上密麻的“七”字刺青——每个都缺了横笔,活像串没晒干的咸鱼。
陆九川趁机摸向樟木匣底层,指尖触到个冰凉物件。抽出来竟是柄断剑,剑柄缠着褪色的辽东军袄布条,刃口锈迹形如麻绳勒痕。裴照雪袖中银针突然颤动,针尾棉线自行崩断——石壁缝隙渗出硫磺水,顺着棉线腐蚀出焦黑的“九”字。
院判的鼾声骤停,花斑猫凄厉的嚎叫震落墙灰。裴照雪拽过陆九川往暗门冲,断剑刃口刮过石壁,擦出一串靛蓝火星。药童突然暴起,染血的脚背猛踹机关,靛蓝布包堆里“轰”地炸开团白雾,硫磺气混着砒霜末糊了满墙。
“闭气!”裴照雪甩出灰鼠裘罩住两人,陆九川的芝麻糖棍卡住暗门机关。白雾中传来院判的惨嚎,麒麟补子金线遇砒霜烧成灰黑,老头儿撞上博古架,钧窑药瓶应声而碎,瓷片里飞出张黄麻纸,户部朱砂印正盖着“盐课亏空七万两”。
陆九川的裤腿被硫磺水蚀出个洞,断剑鞘尖挑着黄麻纸往外冲。花斑猫蹿上院墙,爪钩带倒晾药的竹匾,晒干的益母草天女散花般落下。裴照雪银针钉住竹匾边缘,匾底粘着的靛蓝布屑飘向太医院正堂,布角针脚与慈宁宫毒布如出一辙。
日头偏西时,太医院焦糊味引来巡夜侍卫。裴照雪拢着灰鼠裘跨出院门,袖中银针串着三样新证:虫腹蜡丸、盐引残片、断剑布条。陆九川蹲在巷口啃冻梨,羊皮食单卷成筒插在断剑鞘里,残页上的猫爪“七”字被硫磺熏成靛蓝,活像盖了方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