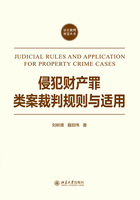
第3章 罪刑相适应原则
一、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定罪时适当考虑刑罚的因素
传统罪刑关系理论认为,犯罪与刑罚之间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为此,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是单向的,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及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必须遵循先定罪、后量刑的时间顺序,不能把量刑提到定罪之前”[47]。从司法实践来看,大量简单案件的办理过程的确如此。然而,在近些年发生的以“许霆案”为代表的“难办”案件中,审判人员沿着上述路径所作出的裁判结果却惹来众怒。为此,有学者开始对传统“由罪及刑”的正向模式进行反思,认为“刑从罪生、刑须制罪的罪刑正向制约关系并非罪刑关系的全部与排他的内涵,在这种罪刑正向制约关系的基本内涵之外,于某些疑难案件中亦存在着逆向地立足于量刑的妥当性考虑,而在教义学允许的多种可能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应的妥当的法条与构成要件予以解释与适用,从而形成量刑反制定罪的逆向路径”[48]。对此,张明楷教授也指出,“几乎在所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检察官通常都是先有一个结论,然后再去找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看这些条文文字是否能包含案件的条件,这就是国外学者常说的三段论的倒置或者倒置的三段论”[49]。同样,笔者在长期审判实践中也发现,在疑难案件的定罪论证过程中,量刑结果实际上提前参与到了对法律规范甚至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当中。由此可见,罪刑相适应原则具有了更多的含义,由传统的罪制约刑的单向关系转为罪刑相互制约的双向关系。基于法定刑对构成要件的反向制约作用,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应当按照典型的犯罪构成沿着“由罪及刑”的正向路径定罪处刑,但如果所得出的结论明显罪刑不相当的时候,我们要调转思路,寻找近似的犯罪构成。
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解释与适用中的体现
在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官适用法律其实就是一个解释法律的过程。我们知道,法律解释的方法有很多,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那么,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我们在何种情况下应当采取何种解释?其理由和根据又是什么呢?“在具体个案中,当数个解释方法分别导出对立的结论时,为了决定应采哪一种解释,方法论长久以来都在努力试着定出各种解释方法之间的抽象顺位,但是并没有成功。对于具体个案中判决的发现来说,这些解释方法仅具有次要的意义。依此,法律适用者是先根据他的前理解及可信度衡量决定正确的结论,然后再回过头来寻找能够证成这个结论的解释方法”[50]。具体到刑事案件中,我们在为某一罪状用语寻找解释方法的时候,需要考虑法条所规定的法定刑以及依此法条最终可能作出的宣告刑的轻重,使解释的结论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关于这一点,正如张明楷教授所指出的,“法定刑影响、制约对相应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因为法定刑首先反映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态度,所以,解释者必须善于联系法定刑的轻重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轻微行为排除在重法定刑的犯罪构成之外,使严重行为纳入重法定刑的犯罪构成之内”[51]。由此可见,在具体理解适用法条过程中,如果说罪刑法定原则为刑法解释划定了边界,那么罪刑相适应原则就为刑法解释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应当采取何种解释方法。
【指导案例】张彪等寻衅滋事案[52]——以轻微暴力强索硬要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被告人张彪在上学期间与同学秦青松关系较好,并曾帮助过秦青松。张彪在毕业联系工作时让秦青松帮忙,因秦不予提供帮助以致心生不满。2007年6月17日17时许,张彪得知秦青松要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的富景生态园游玩,便电话通知被告人韩超到富景生态园“收拾”秦青松。韩超接到电话后,即带着被告人倪中兴赶到富景生态园。在富景生态园,张彪向韩超指认秦青松后,韩超、倪中兴遂上前对秦青松进行殴打。然后,张彪要求秦青松给钱,因秦青松身上钱少,便要走其手机两部,并让其第二天拿钱换回手机,张彪、韩超各带走一部手机。后经秦青松索要,张彪将一部手机归还,但另一部手机被张彪卖掉,赃款被张彪和韩超挥霍。经鉴定,两部手机共计价值人民币1033元。
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来看,其与抢劫罪的构成特征相似,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行为。然而,抢劫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重罪,相对而言,寻衅滋事罪是一种轻罪。寻衅滋事罪通常发生在熟人之间,行为人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精神刺激,故此类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比较轻微,司法机关查处起来也比较容易。但抢劫罪的行为人则往往选择陌生人作为犯罪对象,为了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获取财物,给被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往往也较为严重,侦破查处起来也更加困难。为此,刑法对这两种犯罪行为在法定刑上作出了相差悬殊的规定。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我们在对两罪进行区分时,不仅要考量其犯罪构成的差异,还要凭借社会一般观念,权衡一下对行为人处刑后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以期准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和罪名。具体到本案中,三被告人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与抢劫罪相似,但考虑其实施暴力的程度并未超出寻衅滋事罪所要求的范围,主观上并非单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是出于报复教训他人的动机,以及归还一部手机给被害人、索要财物价值不高,且三被告人中有一人为未成年人,另两人刚刚成年等情节,故法院以寻衅滋事罪认定是正确的。[53]
【指导案例】张舒娟敲诈勒索案[54]——利用被害人年幼将其哄骗至外地继而敲诈其家属钱财的能否构成绑架罪
2006年10月2日13时许,被告人张舒娟在江苏省淮安市开往淮阴的专线车上偶遇中学生戴磊。张舒娟主动上前搭讪,在了解到戴磊的家庭情况后,张舒娟遂产生将戴磊带到南京,向戴磊家人索要钱款的想法。随后,张将戴磊哄骗至南京并暂住在鸿兴达酒店。当晚23时许,张舒娟外出打电话给戴磊家,要求戴家第二天付8万元人民币并不许报警,否则戴磊将有危险。次日上午,张舒娟又多次打电话到戴家威胁。其间,戴磊乘被告人外出之机与家人电话联系,告知其父并无危险。后在家人的指点下离开酒店到当地公安机关求助,淮安警方在南京将张舒娟抓获。
本案被告人张舒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对被害人实施加害相要挟,向被害人亲属索要钱财。从形式上来看,似乎符合勒索型绑架罪的构成特征。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绑架罪在量刑上表达了异常严厉的态度,为避免对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虽控制人质但恶性不大的案件以绑架罪论处并科以重刑,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有必要严格解释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对控制人质的手段行为等进行限缩性解释,将其限定在具有极端性的手段上,从而达到与其刑罚设置相匹配的程度。反之,如果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不足以对被害人形成实际的控制,也没有对被害人进一步实施加害的可能,则不属于绑架罪中的手段行为。具体到本案中,被告人张舒娟在实施绑架行为控制人质过程中,并未对被害人戴磊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主要采取欺骗的手段,使其自愿跟随她去南京,到南京之后亦未对其人身实施任何实质性的限制,出门时也是将戴磊一个人丢在宾馆房间里,致使其可以自由离开酒店到当地公安机关求助,更没有勒索不成要加害戴磊的意图,不符合绑架罪的特征,故法院对其以量刑更轻的敲诈勒索罪来认定是适当的。
【指导案例】林燕盗窃案[55]——保姆盗窃主人财物后藏于房间是否构成盗窃既遂
2006年9月8日,被告人林燕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到被害人支某家中担任全职住家保姆,负责打扫卫生和烧饭,被害人家中共聘请3名保姆。同年9月9日和10日,林燕利用打扫卫生之机,先后3次从支某的卧室梳妆台抽屉内,窃得人民币3480元、价值人民币99800元的各类首饰11件,后将现金及部分首饰藏匿于林燕在一楼的房间写字台抽屉内,其余首饰分装成2小袋藏匿于被害人家中三楼衣帽间的隔板上。9月10日傍晚,保姆李某告知被害人支某,“看到林燕翻过其卧室内的抽屉”,支某发现物品被窃遂向林燕询问,并在林燕房间抽屉内找到现金人民币3480元及首饰,但林燕拒不承认其盗窃事实,后支某拨打110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后,林燕才交代其盗窃的全部事实,并从衣帽间找出藏匿的首饰。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林燕盗窃主人财物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既遂争议较大: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本案犯罪对象系人民币与首饰等小件物品,故当林燕取得并实际掌控之时,就应认定为盗窃既遂。第二种意见认为,林燕的房间属于个人空间,藏于此处的现金和首饰系盗窃既遂;而衣帽间属于主人房屋,主人对藏于其中的首饰具有排他性控制权,系盗窃未遂。第三种意见认为,主人对房屋内的全部物品均具有独立控制权,无论是置于保姆房还是衣帽间,均在主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应认定为盗窃未遂。可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所盗窃财物究竟处于谁的控制之下。其实,我们还可以从罪刑相适应原则出发来认定案件的犯罪形态。本案被告人林燕系来沪打工人员,对财物或者首饰的价值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其利用工作之便顺手牵羊,取得财物后并没有及时转移,也没有立即逃跑;财物最终都被找回,被害人没有受到财产损失;林燕对其盗窃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虽然有认识,但如果知道可能会判处重刑,其未必会铤而走险,这也说明了林燕的主观恶性及其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并不是很大;而如果将林燕的行为认定为盗窃既遂,由于盗窃财产数额已经超过10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超出了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量刑过重。故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出发,法院认定其为犯罪未遂并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是适当的,实现了罪刑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