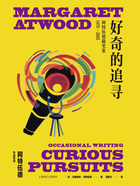
归途
凌晨三点,渥太华和北湾之间的17号高速,十一月。我望着灰狗巴士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窗外。渥太华车站的咖啡还有余味,我在那里被困了四个小时,因为多伦多的某个人看错了时刻表;我坐着写信,尽量不去看几名女服务员赶走一个瘦小干瘪的醉汉。“我天南海北哪儿都去过哪,小丫头,”他在被服务员强行披上外套的时候说,“我去的地方你见都没见过。”
巴士频繁倾斜转弯,车头灯照亮了沥青、撒了化雪盐的路缘,还有深色的树林。我猜想我们会经过那间汽车旅馆,据说是在伦弗鲁镇外的高速路边——但是哪一边呢?——而且我还要步行,可能得走上一英里,带着两个行李箱,里面塞满了我的书,走到哪儿拖到哪儿,因为说不定这里一间书店也没有,但在多伦多又有谁知道呢?一辆卡车经过,被压扁的“加拿大产内容”落满路面,事后警察搞不懂我究竟在那做什么,现在我自己也想弄明白。明天早上九点(九点!)我预定要去伦弗鲁的一间高中办一场诗歌朗读会。在伦弗鲁玩得高兴,多伦多的朋友在我启程前说,语气里带着的,我猜是一丝挖苦。
我想起了夏天,法国的一座游泳池,一个我认识的人仰面漂在水上,解释着为什么不应该让加拿大的银行经理把七人画派的作品挂在墙上——这是错误的印象,满眼大自然,没有人烟——一群身份各异的欧美人满腹狐疑地听着。
“要我说,加拿大,”其中一个拖长了音调说,“我觉得应该把它送给美国,这样就好了。就除了魁北克,它应该送去给法国。你应该搬到这里来住。是不是,你其实已经不在那里生活了。”
我们终于到了伦弗鲁,我走下巴士,踏进六英寸厚的新雪。他错了,假如真有一个我生活的地方,那就是这里。17号高速是我的第一条高速,我出生六个月就沿着它走,从渥太华到北湾再到蒂米斯卡明,从那里又经由一条单车道的土路进入丛林。在那之后,一年两次,冰雪融化的时候向北,开始结冰的时候向南,中间的日子就在帐篷里度过;或是在父亲搭的小木屋里,小木屋建在花岗岩角上,走一英里水路能到达一个魁北克的村庄,那个村庄十分偏远,在我出生前两年才通了路。我已经路过和即将经过的城镇——安普赖尔、伦弗鲁、彭布罗克、乔克里弗、马塔瓦,每个镇上靠着伐木业的利润和以为森林永远不会耗尽的幻想建起来的姜饼屋似的古老宅院——它们是地标,是驿站。不过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高速公路升级了,现在还有了汽车旅馆。对我而言,熟悉的只有夜色和树林罢了。
我直到十一岁才完整地上了一年学。对于这段关于我童年的描述——住在森林里、与世隔绝、四处流浪——美国人通常不会像加拿大人那么惊讶:毕竟高级杂志广告里介绍的加拿大就应该是这样的。听说我从没住过因纽特人的冰屋,我父亲也不像已经停播的(美国)广播节目里的普雷斯顿中士那样大喊“上啊,哈士奇!”,他们有些失望,但除此之外都觉得我的话十分可信。惊到竖起眉毛的是加拿大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伦多人。仿佛我是他们自己觉得不光彩、不真实,或是根本无法相信曾经发生过的过去的一部分。
以前我从没在高中开过朗读会。一开始我害怕极了,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我嚼着抗胃酸咀嚼片,一边回想自己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对来访的大人物做的那些事情:没礼貌的窃窃私语、吵闹,如果能逃脱处罚的话还会扔橡皮筋和回形针。他们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也不会有兴趣:我们的高中教学里没有加拿大诗歌,几乎也没有其他任何关于加拿大的内容。高中前四年我们学了希腊、罗马、古埃及,还有英格兰的王朝,到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在一本主要讲小麦的暗蓝色书本里学到了加拿大。一年当中有一次,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会过来,念一首关于乌鸦的诗;念完之后他会卖自己的书(和我即将要做的事情一样),用蜘蛛腿一样细长的字迹给书签名。这就是当时的加拿大诗歌。我在想我看起来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脆弱,不合时宜而且多余。他们真正的活动——真正的活动——难道不是今天下午的足球赛吗?
提问时间:您有想要传达的信息吗?您的头发确实就是这样的吗,还是做了发型?您的构思从哪儿来?写作要花多长时间?这是什么意思?您会觉得不自在吗,像这样把自己的诗读出来?我会不自在的。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我能把我写的诗送去哪里?我想发表。
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的,有些答得短,有些答得长。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问了,他们想要讨论:在我的高中是不会有提问的。而且他们还写作,他们中的一些人。难以置信。我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想着,觉得自己很老。
在迪普里弗我住在一个我母亲那边的远亲家里,他是一个科学家,长着不近人情的蓝眼睛,轮廓分明的前额拱起,还有母亲那边的亲戚们个个都有的新斯科舍省鹰钩鼻。他带我参观了他工作的原子研究场;我们穿着白色的大褂和袜子,以防受到辐射,站在14英寸的镶嵌玻璃后面,看着一只金属抓手搬运看起来完全无害的东西——铅笔、金属罐头、一张纸巾。“在里面待上三分钟,”他说,“你就没命了。”无形的力量令人着迷。
在那之后我们查看了河狸在他家房子上搞的破坏,他还给我讲了一些外祖父的故事,那是汽车和广播还没有出现的年代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些故事,所有的亲戚我都会向他们打听,它们给了我一条纽带,哪怕再脆弱,却能让我连接过去,连接起一种由人、人际关系和历代祖先,而不是由物品和景象所组成的文化。这次旅程让我听到了一个新故事:外祖父彻底失败的麝鼠养殖场。养殖场有一道围绕沼泽地仔细修葺的围栏,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更容易把麝鼠聚集到一起;但我的表亲说,被他关在围栏外面的麝鼠从来都比外祖父赶进围栏里的多。一个农户在上游倾倒了一些苹果树杀虫喷雾,麝鼠被全数消灭,生意也失败了;不过当时大萧条来袭,麝鼠市场本来也已经跌破了底价。那道围栏如今还在。
有关外祖父的故事大多都是成功的,但我把这个故事也加进了我的收藏里:当家族图腾难以寻觅的时候,关于失败的故事就有了它的位置。“你知道吗,”我对表亲说,告诉了他一个最近从外祖母那里收来的传说,“我们的一位女祖先曾经被人当成女巫而被浸到水里?”这件事情发生在新英格兰;她究竟是沉到水底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还是像女巫一样浮了起来,并没有留下记录。
他家客厅窗外,渥太华河对岸,那密实的树林,是属于我的地方。或多或少算是。
夜里下了冻雨;我把行李箱放在雪橇上,在薄冰上拖着走了两英里,赶到下一场诗歌朗读的地点。
我到了北湾,因为雨夹雪迟到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我在秘密共济会的会堂里开朗读会,在一个地下室里。组织朗读会的大学老师们很紧张,觉得不会有人来,北湾以前从来没有办过诗歌朗读。这个镇上人人都看过那部电影,我对他们说,你们不用担心,而且事实上朗读会的前十五分钟他们一直在忙着加椅子。这里来的不是学生,而是各式各样的人,老的,少的,一个以前和我们一起在魁北克住过的母亲的朋友,一个叔叔在湖的尽头经营钓鱼营地的男人……
下午我接受了本地电视台的采访,采访我的男人脊背挺直,西装紧绷。“这是什么东西,”他态度冷淡地拎着书角晃着一本我的书,向观众展示他对诗歌不感兴趣,阳刚气十足,“儿童读物?”我提议说假如想知道书里写了什么,他或许可以试着读一读。他火冒三丈,说自己从来没有被这样侮辱过,就连杰克·麦克莱兰来北湾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态度恶劣。电视台没有播采访,改播了一个关于蔬菜面条的专题节目。
在那之后,在三十场诗歌朗读会之后。我在纽约读了一首写到户外厕所的诗,不得不解释户外厕所的意思(还有两三个人事后偷偷摸摸地走上来说他们也曾经在户外……)。遇到了一个从没见过奶牛的人;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出过纽约城。然后和他讨论加拿大和美国究竟有没有区别。(我去过的地方你见都没见过……)在底特律,努力地解释,在加拿大,出于某些奇特的原因,并不是只有其他诗人才会去参加诗歌朗读会。(“你是说……像我们的妈妈这样的人也读诗?”)听一个人对我说或许我作品里称得上“优势”的是吸引人的“区域性”特质——“你知道的,就像福克纳一样……”
在安大略省的伦敦,那一年的最后一场朗读会,说不定也是,我心想,我的最后一场朗读会,我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像台留声机了。一位女士:“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我从没觉得自己这么不像个加拿大人。”另一位女士,年纪很大了,眼神敏锐得让人吃惊:“你是借助比喻思考的吗?”另一个人:“什么是加拿大的身份认同?”大家似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何才能把所有这些,在你我的脑中维系到一起。因为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所有人生活的地方:不只是一个地点或一个地区,虽然这么说也没错(我还可以加上温哥华和蒙特利尔,我在这两个地方各住了一年,还有埃德蒙顿,我在那里住了两年,还有苏必利尔湖和多伦多……)。它是一个由影像、经历、气候,以及你自己和你祖先的过去所共同组成的空间,说出口的话语,每个人的长相,以及他们对你的行为作出的反应,重要的和琐碎的事情,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清晰。形象是外在的,它们存在着,是我们与之共同生活且必须应对的东西。但是判断和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必须在脑内做出,它们由文字构成:好的,坏的,喜欢,讨厌,是去,是留,要不要继续在这里生活。对我而言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探索我事实上究竟生活在哪里。
我认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加拿大更是一个人主动选择住下来的国家。我们要走很容易,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了。可以去美国和英格兰,课堂上教的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比我们自己的历史更多,我们能够融入其中,成为永久的游客。在加拿大一直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倾向,拒绝相信自己的现实经历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在“真正”的地方,比如纽约、伦敦,或者巴黎,生活才能变得有意义或有价值。这同时也是一种诱惑:在法国那座泳池的对话不能不说是冷静客观的。问题永远都是,为什么留在这儿?而且还不得不回答了一遍又一遍。
我并不认为加拿大比其他地方“更好”,同样也不认为加拿大文学“更优秀”;我生活在加拿大,阅读加拿大文学,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它们是属于我的,包括其中所有与地域相关的意识和观念。拒绝承认你来自哪里——其中必然包括面条男人和他的敌意,以及反民族主义女士和她的疑虑——是无异于截肢的行为:或许能够借此自由飘荡,成为世界公民(还有哪个别的国家以此作为理想?),却要付出手、腿或是心的代价。找到自己的所属之地,就能找到自己。
然而还有另一番来自外界的景象和真相,我必须去适应。这片领地,这件被我称为“我的”之物,属于我的时间或许不多了。少有哪个国民比加拿大人更加热忱地推销自己的国家,这也是反复探求的加拿大身份认同之中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买家,像大家说的那样,愿意开采我们的资源;买家总是有的。需要关注的是我们渴望兜售的急不可待。开发资源和开拓潜力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源于贫乏,仰赖于金钱,而后者源于内在,其原因我只消犹豫片刻,便会称之为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