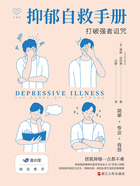
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些模型
1.过度活跃的超我
我觉得人们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评价有失公允。虽然现在看来他的一些理论很奇怪,但它们往往是被夸大和戏谑化的。在一个世纪前他研究这方面的理论时,重度抑郁障碍的标准疗法包括将病人用锁链拴在墙上、用高压水枪猛浇或是将病人绑在一个能旋转的椅子上长时间地高速旋转。
“你觉得好一点了吗?”
“我好了,我好了,求求你,别再弄了!”
于是,治疗就“成功”了。
弗洛伊德置身于如此的临床环境之中,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说法,诸如“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成年人取决于我们生命早期的经验,而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则决定了日后我们的心灵运作的方式”。这些放在今天都是不言自明的事,但在当时却都是第一次出现的理论,它们可能也是在20世纪早期推动对心理障碍的治疗方式由监护式转变为治疗式框架的重要因素。
下面我会主要谈谈其中的一个概念——超我(superego)。弗洛伊德将心灵分为三个领域: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本我是指我们所有人都有的原始部分的自我,包含有诸如为争夺资源而争斗、交配以及寻求即时的快乐与满足的各种未受良知抑制的冲动。自我是心灵所有部分的中心的综合,就是自性(self),即“这个是我”。超我指的是良知,这个部分负责抑制本我并让我们能做到自控、言行得体。
心灵的这些部分在人生的早期就形成了。超我是通过父母让成长中的儿童明白一个道理——他的冲动的满足是有限的这一点来形成。如果他的父母坚定而温和,他就会形成一种完好的道德心理,日后也会拥有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
然而,如果他的父母严苛而又喜欢折损人,可怜的孩子就得背负着过度的拘束与自责长大。这是对糟糕的父母们形成强烈依恋的孩子们身上屡见不鲜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作为一位成年人,一位慈母的儿子往往不会对自己的母亲给予太多关注,甚至他可能要靠妻子提醒才想起在妈妈生日那天给她拨个电话问候。而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暴君的后代则需要向她奉上永恒不渝的爱与关注。电视上曾经播出过一档由罗尼·科贝特(Ronnie Corbett)出演的名为《对不起》(Sorry)的喜剧节目,我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因为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真实了。罗尼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位名叫Timothy、45岁却仍旧单身的男子,他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他那可怕的妈妈在操控人上很有一套,儿子的一举一动她都要管,而他的爸爸为了躲老婆,则早早地一心钻到盆栽棚里。Timothy 遇到了一个好女人,他的妈妈就破坏他们的感情,好把他儿子留在自己身边。他的女朋友恼怒地问他:“你为什么允许她这么做呢?”
他回答不出来。其实,这个答案很明显:他的人生就是一番为博得他妈妈的爱与认可的注定失败的努力而已。他永远都不会成功,因为他妈妈根本看不到她自己的需求与愿望之外的东西。要是她看得到,儿子长大之后就会自信、开朗,早就离开她了。
另一个神奇之处则是当这种父母去世之后,这类被桎梏住的成年子女不会享受自己获得的自由,而是会继承他们的角色,变得更苛责和否定自己。就好像严苛、折损人的父母被扛在了他们的肩上,在没完没了地给他们讲他有多么不堪、多么一无是处一样。这就是一直在他们身上侵害他们的超我。他们将自己的人生都专注在他人的需求上,很快就会发觉有很多人在对他提出要求,因而保险丝就开始过载了。
所有的模型都能推出结论。这个模型说明,在拒绝苛责你的父母或是超我的价值观、论断和各种预设之前,你都是不会开心的,还会一直生病。所以,请立刻采取行动,让自己拥有时间、空间和欢乐吧。如果这么做你会有负罪感,请随它而去。我会在后文中告诉你如何将负罪感转变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但是你必须先作出改变,因为没有变化,一切就会照旧,那就太糟糕了。
2. 内化的愤怒
大多数精神动力学或是探究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将抑郁障碍视为一种针对自我的愤怒。处理愤怒的途径就那么几种,你可以不加隐瞒地将怒气发泄出去,但这样往往会让你惹上麻烦,让其他人疏远你。你也可以对其进行升华(sublimate):意思就是说,化愤怒为充满活力的行动,例如运动、在工作上竞争或是搞艺术事业。很多领域中成功的人发起脾气来都很狂暴。你还可以凭全面的自信阻止愤怒的产生,当然这里所说的自信之心与为人霸道是完全相反的两回事。一个自信的人不加张扬而坚定地追求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明白什么是能接受的,什么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的需求会得到满足,也就没有理由生气或者激动。而反之,不自信的人,就不能或者不愿明白地说出他的需求。因此,当他被忽视、遭到欺骗或者他所做的事被别人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就会气得冒烟。最终,这积累起来的愤怒再也无法抑制,于是他大发雷霆,将其发泄出来。有时候,这类人会让酒精产生作用——我的一些病人会故意把自己喝醉,因为这是他们释放自己挫败感唯一的途径。不幸的是,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与他人关系的破裂。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压抑自己的愤怒:也就是说,将其深深地置于脑后。早年成长不顺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这招。这在那时是一种必备技能,但不幸的是,日后当发现它是在帮倒忙的时候想摆脱却往往已经做不到了——出身于公立学校的我们这一代乃至更年长的人很多都是这样。无事发生的时候,那些本应该懂得这一点的人(比如我们的配偶)跟我们说这都挺好的。但是,当空气中带着情绪的味道时,一道隐形而无法穿透的障碍则会重重落下。理由很简单,在过去,寄宿学校都是相当残忍、孤独的所在。我还记得,第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被撂在学校的我看着父母的汽车消失在路上,想到他们一个月都不会再出现时,心简直都要碎了。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父母这样离开可能就跟他们永远不会再来了一个样。在那天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离别与失去,但没有一回像那时那么凄凉。所以,在这种地方,我们很快就会学会将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尤其是悲伤的感情,因为暴露出的任何脆弱都可能会被人抓住,在宿舍生活中占我们的便宜。在啄序(pecking order)的形成上,悲痛、伤感、恐惧、孤独、愤怒……各种负面情绪会不可避免地越积越多。
寄宿学校情感控制的产物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种人看起来似乎波澜不惊,而且很少与人争吵。但是,既然他所处的环境不接受他的情绪(无论是出于这样那样的什么原因),平时积累的愤怒就得要另寻出口。有时候,愤怒会向内指向他自己,他就会为越积越多的问题而责备自己,一次次通过加倍的努力寻求解决,当然也就开始让自己过载。他的超我开始攻击他的自我,这时候他的边缘系统就嘎嘎作响了。
这种情况并不只是针对公立学校的学生们,它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在那些孩童时代就被始终如一地爱着、呵护着的人身上就很少出现。对父母们来说,其中的寓意很明白:孩子不需要吃苦头。经历困苦之后,孩子可能看起来是变得坚强了,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孩子现在越来越坚强,日后脆弱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他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的爱、温暖与扶持,真正的坚强是通过温存来培养的(strength develops through tenderness)。
对于已经意识到自己倾向于压抑诸如愤怒这样情感的成年人来说,可以试试改变自己的想法(change the way you operate)。在后面谈“能行”(OKness)的时候我还会提到这一点,但眼下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如果你一直任由愤怒或是别的负面的情感堆积,以后遇上事的时候它们可能就会跳出来攻击你。
3. 与过往损失共鸣
人们往往不会头一次碰上糟心事就生病,特别是孩子,看起来似乎无论你把什么扔到他们头上,他们都能若无其事地接住,适应力堪称惊人。比方说,一个因为癌症而失去了爸爸的十二岁的小姑娘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抑郁。她在那段时间可能会变得黏人、焦躁或不太听话,但是如果家庭中其他长辈处理得当,过一段时间,她会恢复自己原来的样子,除了会想念她爸爸之外,表面看不出来存在什么问题——在她童年剩下的时间里是这样的。可是,20 年之后,等她从她那令人艳羡的工作岗位上被裁下来时,很快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障碍。
这是怎么回事呢?失去工作跟失去父亲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在象征的意义上,两者有很多相仿的地方——两者都与心中预设的安全感与确定性的崩塌有关;两者都涉及失去宽慰感与自尊的源泉;两者都让她感到迷失和孤独。她的这次被裁与她早年失去父亲的经历产生了共鸣——它在过去的20年间都在沉睡,被一个那时还不懂得悲痛且吓得够呛的孩子压抑着。
在我看来,避免陷入与过往负面经历产生共鸣的抑郁的方法就是严肃对待自己和自己的感觉(feelings)。我见到过很多人,他们在因为丧失亲友或是其他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而手足无措的时候,会斥责自己不够坚强,太过软弱,然后会为了硬挺住而强迫自己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那么,他们此时的不畏艰险和顽强拼搏如果持续下去最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用猜就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请相信你的感觉,正视它,可能的话,找一个你能信赖的人,对他倾诉、发泄。
4. 自恋
这个概念会出现在一本讲解抑郁障碍的书中还真是出人意料!大多数人认为自恋的人是爱自己的,而不是像产生这个术语的典故那般不可理喻。然而,用心理学的话来说,一个自恋者根本不爱自己,实际上他们对自身是一种厌恶和鄙视的情绪。
让我先把你带到一间有个婴儿在哇哇大哭的育儿房里来。这个婴儿已经哭了有一会儿了,父母都没有听到她哭,因为他们正忙着在楼下喝酒。婴儿的哭声开始升高,越来越愤怒、绝望,脸也开始发红。生物学设计出这种恼人的婴儿发出的噪声为的就是让父母们赶紧行动起来。但这对父母没有听到,因为他们喝得太多了。婴儿接着一直哭,哭得让人感觉她都要爆炸了。忽然,她停下不哭了。过了一会儿,如果你拿一个响尾蛇或者别的什么玩具去逗她,会发现她直勾勾地盯着你,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你看,她已经过了愤怒和绝望的阶段,进入了一种如我的一位心理治疗师同事所说的“懒散区间(the idle interval)”。这是一种一切感情和伤痛都过去了之后的心理空间。她试过与这个世界进行互动,但是无法融入,于是她除了缩回自己的内部世界,别无选择。
随着她渐渐长大,不时地还会试着从身边的人那里获得一些东西。父母有很多与孩子进行情感互动的机会,想必你听到这会很高兴,因为你不必做凡事有求必应的父母。实际上,有证据显示,发展最为均衡的人的父母往往只是做得“足够好”,而非凡事都尽善尽美。理想条件下,孩子有时候会经历挫折,应该会懂得世界并不总是按你希望的方式运转。但是只要你等待,好事最终会发生的。
可是,这个孩子从未从她那对醉醺醺的父母那里受到过任何持续的关注,所以她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了自己的内在世界中。上学给了她一次新机会,她开始试着通过卖弄自己赢得来自同龄人的关注与认可。但她还不懂得通过将自己对他人的喜爱和兴趣表达出来,以此来让他人喜欢自己。因为太不善交际,她往往都是在遭到无情的拒绝后又溜回她那个空闲的间隔里待上一阵子,就这么时隐时现地度过了童年。但是因为她没有与人交往,没能和同龄人一样学会种种社交技巧,就这样,她寻求关注的尝试一次比一次不顾一切,而她的努力却越来越难以得到回报。于是她几乎一直就是个孤僻、不快乐的孩子。
当她成为一位成年人时,平时会表现得很黏人,但是却不懂得如何让别人开心。她总是用力过猛,对任何逆向的或是自己认定的怠慢都依然用情感上的“闪人”来回应。于是,她工作上的、消遣上的和个人交往上的人际关系就都失败了。她加大努力在各方面弥补,却觉得自己更加一文不值。这之后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桥段了——保险丝的熔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如果你从这个人身上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意识到这不是你的错。你的问题来自你的背景,而不是你的什么缺点,于是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允许自己学着做一些事。现在你其实还不懂得如何对他人感兴趣,但是你得做感兴趣的人会做的事,理由就是人们喜欢对他们感兴趣的人。
我讨厌派对。对那些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最糟糕的派对,我一般都会装成另一个人的样子来混过去。我最拿手的是当一个捧哏(cue-giver),这样在整场派对中除了给人递一递我在心理治疗训练中所学的那些话茬儿之外就连一句真话都不用说。这些话茬儿包括——“真的哎?”“我的天啊”和“这真是绝了,你太猛了!”。此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比如:“原来是这样的?就连在南半球也是这样?”派对过后,其他的宾客们每每都会跟派对的主办人说:“他可真是有意思,妙极了。我可是还什么都没说呢。”
我怎么会这么招人爱呢? 答案就是大多数人都渴望得到聆听和认可。如果你刚刚开始试着让别人注意到你,就装作对他们感谢兴趣吧。这不是骗人。正如你会在后文中所见的那样,你的行动会让你做出改变,也会让这个世界更多地奖励你。别再那么用力过猛了,你不需要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