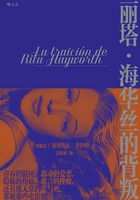
第1章 来自潘帕斯草原的梦幻骑士——普伊格
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Juan Manuel Puig,1932—1990)出生于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区的比耶加斯将军镇(General Villegas)。从小在中产阶级的环境中成长。他的父亲巴多梅洛(Baldomero)是当地的红酒经销商,母亲玛蕾(Malé)则是一直在药房工作的职业妇女。他的母亲即来自本小说里提到的拉普拉塔,念过大学,在当时来说,算一位知书达礼的女性。从小说里米塔这个角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普伊格是以他母亲作为创作原型的。
普伊格从小就很黏母亲,一直到离世前都跟母亲相依为命。小时候,他母亲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经常带着普伊格到电影院去看星期三下午场的电影。因为他喜欢跟着妈妈去看文艺爱情片,加上他从小喜欢玩过家家,普伊格在学校经常遭到班上同学的取笑和欺负。他父亲为了能让他的个性变得更有男子气概些,开始禁止他每个星期都去看电影,只准他每个月去一次。所以普伊格从小就跟他父亲比较有距离感。尽管普伊格提到他父亲时,总是含蓄地说:“他其实是个好人。”
拉丁美洲著名小说家略萨在一篇评普伊格的文章中提到,对任何一位敏感的男孩而言,生活本身必定是个很残忍的世界。特别是在一个充满大男子主义且充斥着偏见的拉丁美洲南方小镇。[1]
对普伊格做过相当深入研究的传记作者苏珊娜·吉尔·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则表示:“普伊格从小就学会了一种逃避现实世界中的残忍、悲惨的方法。他系统地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虚构世界,直到变成他自己的真实为止。”而他的虚构世界并非从书本而来,而是跟母亲去电影院看电影得来的。另外,普伊格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的。在母亲下意识的保护下,他更是狂热地爱上了电影的世界,于是根本就不想活在真实世界里,而且会尽最大的可能活在电影梦幻世界里。
普伊格经常会快乐地回忆起他第一阶段的童年。只是这个备受保护的童年在他十岁时就消失了。因为1934年,他的弟弟刚出生不久就不幸早夭。从小说里关于早逝小孩的描写,可看到作者对弟弟早夭的不舍与怀念。十五岁的时候,一个男同学还曾试图强暴他,从此他幸福的童年时光就提前结束了。
普伊格和小说中的主角多多一样,是个功课非常好的学生。由于比耶加斯将军镇没有中学,后来他被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一所中学去读寄宿学校。他自己倒是很高兴能够到首都去念书,因为这样周末就可以去看电影首映、轻歌剧、歌剧,逛博物馆,看戏和散步,等等。这样的活动在他童年所居住的小镇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奢求。
所以普伊格从十八岁离开家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甚至连故土阿根廷都没有回去过。直到他1990年在墨西哥过世,他的弟弟为了让他能与一辈子相依为命的母亲相伴,决定把他的骨灰带回阿根廷,他都没有再踏进国门。[2]在1989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记者问到他为何不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阿根廷军队政权垮台之后返乡?普伊格回答道:“或许是因为我的作品在全世界都获得了广大的反响,而阿根廷的媒体却始终对我进行封杀且只字不提伤透了我的心吧!”[3]
小说情节发生的背景科罗奈尔巴列霍斯(Coronel Vallejos),几乎就是普伊格童年成长的故乡比耶加斯将军镇的真实翻版。而横跨小说、影评界的古巴作家因凡特则认为,其实普伊格真正的出生地是在电影里,也就是说,他其实生于梦幻之家。普伊格对电影如痴如醉,以至于一生都宁愿流连于电影银幕中。电影也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梦幻世界之门。电影是他的私密空间,也是他自我保护的永恒秘密花园。
为了把这位20世纪40年代的红发尤物,也是好莱坞电影女明星丽塔·海华丝[4]的名字写入他的小说书名,普伊格曾写信给她本人,信里他如此介绍自己的小说:
这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于1933到1948年的阿根廷,地点是个从首都得坐十二小时的火车才能到的潘帕斯草原小镇。住在那个小镇,对外唯一的真实就是活在电影的世界里。只有当电影开演、灯光亮起,还有电影明星的名字打在银幕上时,小男孩的生命才鲜活起来,然而这些璀璨貌美的女明星也成为他内心世界冲突的开始……[5]
小说里的男孩多多,从小就是个电影迷,并且与母亲形影不离,这其实就是普伊格自己真实生活的反映。普伊格也从来没有否认他这部处女作的自传性质。有一次他接受法国同性恋杂志《面具》(Masque)的专访,被问到小说里这个从小敏感的男孩,普伊格慵懒地一个字一个字地以法语缓缓说出“Toto,cést moi”(“多多,就是我”)。
普伊格成名后,各种邀约不断。卡布列拉是他的多年文友,曾奉劝普伊格最好找个经纪人来处理他在电影、戏剧、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繁忙邀约。普伊格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我才不需要什么经纪人呢!我天生就是个专业的管家婆!”普伊格还跟他拍胸脯保证,他的守护天使总是会帮他读那些写得密密麻麻的合约条文。
卡布列拉还提道:“普伊格彻底地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尽管他一生都‘为情所苦’,但他的性格其实是幽默且极端自嘲的。在写信给友人时,他时常称自己是萨莉(Sally),也就是影星丽塔·海华丝的电影《不是冤家不聚头》(My Gal Sal,1942)中的女主人公。因此,如果大家想了解普伊格自称为萨莉的个人世界,那么阅读《丽塔·海华丝的背叛》这部小说是最佳选择。”
普伊格一生情史不断,但都不持久。过世前不久,他还哀怨地跟友人说自己总是“遇不到好丈夫”。他也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必要“出柜”,因为他早在“柜子”造好之前就出生了。虽然生为男儿身,但他一生宁为女人。对普伊格而言,女人不仅仅比男人更优秀,而且有着男人没有的美丽灵魂。总之,他和作家田纳西·威廉斯一样,都是男人,也都是作家,但都不想活在真实世界中。
小说家略萨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也说:“在所有我认识的作家当中,普伊格是对于文学谈论最不感兴趣的。他从来不会在聊天中引述哪位作家或是哪部文学作品。每当文学的话题出现在聊天中,他都会变得不耐烦,并且转移话题。”
一如苏珊娜·吉尔·莱文在她写的普伊格的传记中所证实的那样,普伊格某一段人生中的确曾奋力阅读文学经典名著,然而他自己的创作主题却好像与这个事实互相矛盾,也就是说,他的创作中经常充斥着各种电影、影星、表演、流行音乐和八卦新闻等。大部分时候,他就算提到了文学,也只是略提及作者,而不谈他们的作品。
莱文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据说一位年轻的阿根廷作家曾造访普伊格在里约热内卢的家。他惊奇地发现,在普伊格的公寓里,大约有三千多部影片典藏,却只有很小一部分的书籍。而且,除了一些他自己的作品和各国译本,其他都是电影制片、导演或演员传记方面的书籍。
在生活方面,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搬到不同的国家居住,对于在一般人看来煞费周章的跨国搬家,他却像是搬到隔壁一样不以为意。他一生住过阿根廷、意大利、墨西哥、法国、美国、巴西,也经常在全世界各处旅行。他离世前居住的最后一个城市是墨西哥城。
有趣的是,在翻译这部《丽塔·海华丝的背叛》的一整年时间里,我个人也刚好从亚洲回到欧洲。因此译稿是历经欧亚两地咖啡香气的熏染才告完成的。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工作的时候,我的耳畔总是音乐缭绕。似乎音乐与文字,最能即刻带着我进入作者文本中的情绪。而且在这部小说的翻译过程中,我的“工作音乐”始终是拉丁音乐:从探戈到波莱罗,古巴老乐人的吟唱与乐器演奏,等等。
还记得翻译这部小说的前半段,多数是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咖啡馆进行的,对面刚好是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外墙是一大片马赛克彩色瓷砖,上面有幅高达三层楼的人物壁画和巨幅《圣经》金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时常,这句话宛如某种力量激励着正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翻山越岭”的我继续往前迈进。许多时候,当我被小说里大量的阿根廷流行方言、俚语困住时,总会抬头凝神思考对面教堂墙上的话语,然后再低头工作。至于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当地黑话,还得等到来了欧洲,请教阿根廷人之后才得以解码。
翻译过程中,我不时会惊叹普伊格写作的想象力是如此旖旎瑰丽,也时常乘着作者想象的翅膀,与他一同翱翔在绮丽的想象星球之上。每当译到作者纵情描写故乡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辽阔场景的段落时,思绪仿佛也随着他的文字神游了广阔的南美大地,那里有草原、绿树、花香及日光美景。许多时候,我也因着翻译小说人物无尽的独白、低语而感同身受,甚至浑然忘我地融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译者仿佛是在用另一种语言临摹文学大师的鬼斧神工。而让译者愿意挑战文学翻译这种超级任务的前提是,原创作品至少必须是一部佳作或经典,这样才能说服并吸引译者为之呕心沥血,推敲再三。尽管要完美地以中文表达原作并且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是一件几近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已经尽力挑战自己的极限,无论是在体能与智力方面,还是在语言技术方面。终于,这份译稿将要付梓。想象着读者与文本相遇之后,或欣喜对话,或赞叹,或评论,我内心尽管忐忑,却仍是喜悦的。
最后,我要向巴塞罗那的阿根廷建筑师友人亚历杭德罗·贝塞罗(Alejandro Beceyro)为我解答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特有的方言、黑话等用法方面的疑惑致上谢意。
注释
[1]Mario Vargas Llosa,“Disparen sobre el novelista”,Clarín,Domingo 7 de enero de 2001.
[2]Daniel Molina Clarín,“Manuel Puig:La maldición,la fama y el exilio”,Domingo 02 de julio de 2000.
[3]Giovanna Pajetta,“Entrevista a Manuel Puig”,Crisis,N°41,abril de 1986.
[4]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1918—1987),美国著名女演员,20世纪40年代红极一时,有“爱之女神”之称。
[5]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Sueños de cine,historias de Novella”,Clarín,Domingo 7 de enero d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