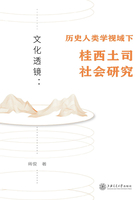
二、文化语境:瘴之分类及时空布局
人们在对瘴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复杂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分类其实是与瘴病的治疗分不开的。为了找到对症下药的依据,必须对瘴按性质分门别类,也才能施以不同治法,这符合中医学的原理。因而这里瘴的类型学既属于地理学性质,也属于医学性质。但总而言之,不管何种瘴气都是危险的,若不治疗,常能置人于死地,这种描述充斥着文学以及医学书籍中。
一种观点认为,瘴气的发生与季节的转换有密切关系。其时气候异常,加之在南方合宜的条件下自然界一些植物极端繁茂,不利于空气的流通,因之产生瘴气。邝露在《赤雅》指出四种以植物命名的瘴气以及成瘴的原因:“春曰青草,夏曰黄梅,秋曰新禾,冬曰黄茅,皆乘草木蓊勃,日气歊焮所成,而青草、黄茅最为毒烈。春夏之交,草长而青,秋冬之交,草衰而黄。二时气候不常,蕴隆重衿,臈月挥扇,咄嗟呼吸,冬夏便分。且桑中卫女,上宫陈娥,偷香窃笑,其不死者幸而免。” 清人闵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种:“又有曰桂花、菊花青。四时不绝,而春冬尤甚。”
清人闵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种:“又有曰桂花、菊花青。四时不绝,而春冬尤甚。” 这些种类的瘴气因普通植物而产生,较为常见。
这些种类的瘴气因普通植物而产生,较为常见。
清代医学家俞震曾长期生活在岭南地区,对于瘴气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古今医案按》所列举的瘴气种类最为全面。首先他将之分成“阴瘴”与“阳瘴”两种:
闽之仙霞,粤之庾岭,阳闭于阴,阳瘴为多。粤西近高雷廉者,粤东之余气,证亦相似,其庆远、柳州、太平,近于交趾诸郡,千山万壑,屏障于南,反阻塞其阳威之气,为山之阳,阴闭于阳,每成阴瘴,阴湿蕴毒,故阴瘴尤重也。
又根据不同事物的影响而成将其分为如下多种:
寻常瘴。春夏之交,乍寒乍热,其气忽然蓊郁,忽然发泄,更衣不时,感冒不一……
暑湿瘴。闽粤有之。春夏之时,久雨阴湿,忽然暑热山岚之气,自下蒸上,人在气交之中,有一种胀闷不可当之势,此即瘴疠时也……
毒水瘴。粤西于云贵接壤处,有水能毒人。其山产五金,皆有毒,况产五色信石者乎……
黄茅瘴。三四月,草深堰俯,久雨湿烂。而时令蒸郁,其性上炎,一种郁勃之气,人虚入口鼻,即患瘴闷……
孔雀瘴。五六月,雨水泛溢,有孔雀处,其屎积于木叶茸草间,随涧水流下。人误吞之于炊爨间,必患腹胀而痛闷……此广西庆远、思恩、太平近交趾处居多,镇远、泗城州、柳州亦有之。
桂花瘴。全州、桂林、梧州、平乐皆有之。八九月间,香气如桂,此瘴最急,触人口鼻即倒仆,此为中瘴……
蚯蚓瘴。二三四月,泥水泛滥,人犯之,腹胀疼楚,如蚯蚓状者,青筋蟠现于肚腹,兴起痕高……
蚺蛇瘴。三四五六七月,蚺蛇交媾,秽浊之气,顺水流下。人或犯之,胸腹胀痛异常,口鼻有腥气……
俞震的归类,部分或有道理。根据我们现在的常识,季节轮换之时最易爆发诸如流感之类的病疫,南方的春天湿度大,冷暖无常也是发病的绝佳时机,即使平日一些地区性疾病的流行,或者人们不能适应环境所导致的疾病,在当代中医临床中尚能见到,论及原因以瘴气之名来解释倒也无妨。不过其中也有许多臆想生造之物,道来稀奇古怪,匪夷所思,令人费解,似乎不足为信。譬如蚺蛇瘴,就大有文章。
考之蚺蛇,在古文献不乏记载,但多被表述为一种十分荒唐可笑的怪物。清人俞蛟《梦厂杂著》所录综合了前人很多说法,较具代表性,曰:“粤西南、梧诸郡,产蚺蛇,大者合抱。在当日已绝无仅有,今所见者,粗围经尺而已。性最淫,见妇女,必追之,蟠绕不解。被交者多死,或产蛇。故村妇樵采于山者,必视路之远近,而量系裙之多寡。遇蛇追及,则解覆其头而奔。少顷,蛇觉复追,解覆如前。倘道赊裙尽,则不免矣。然畏葛藤,捕者系藤其颈,牵之如犬羊……” 且不说蚺蛇瘴是否有之,有关蚺蛇习性的描写近乎志怪神话,所遵循的文化逻辑,似乎是为了神秘化边陲原始的野性以及令人恐惧的力量罢了。
且不说蚺蛇瘴是否有之,有关蚺蛇习性的描写近乎志怪神话,所遵循的文化逻辑,似乎是为了神秘化边陲原始的野性以及令人恐惧的力量罢了。
从历史上看,人们对于边陲一向过度诠释。《魏书·僭晋司马叡传》描述东晋南方地区状况时说:“机巧趋利,恩义寡薄。家无藏畜,常守饥寒。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瘴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 周去非将岭南一些地方形容为“大法场”或“小法场”:“岭外毒瘴,不必深广之地。……昭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若深广之地,如横、邕、钦、贵,其瘴殆与昭等,独不知小法场之名在何州。尝谓瘴重之州,率水土毒尔,非天时也。昭州有恭城,江水并城而出,其色黯惨,江石皆黑。横、邕、钦、贵皆无石井,唯钦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产毒药,其类不一,安得无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运气如中州之疫然。大概水毒之地必深广。”
周去非将岭南一些地方形容为“大法场”或“小法场”:“岭外毒瘴,不必深广之地。……昭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若深广之地,如横、邕、钦、贵,其瘴殆与昭等,独不知小法场之名在何州。尝谓瘴重之州,率水土毒尔,非天时也。昭州有恭城,江水并城而出,其色黯惨,江石皆黑。横、邕、钦、贵皆无石井,唯钦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产毒药,其类不一,安得无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运气如中州之疫然。大概水毒之地必深广。” 南宋释继洪则撰《续附蛇虺螫蠚诸方》,对开具治疗南方各种怪虫叮咬药方的描述,使模糊的情况更为具体化起来:“五岭之南不惟烟雾蒸湿,亦多毒蛇猛兽,故前贤有诗云:‘雾锁琼崖路,烟笼柳象州,巴蛇成队走,山象著群游。’又《编类集》及《岭外代答》《本草》诸书备言广郡多蛇虺、蜈蚣。愚既表出瘴疠论方,又不得不附治蛇虺螫蠚数方,以济人之缓急。”
南宋释继洪则撰《续附蛇虺螫蠚诸方》,对开具治疗南方各种怪虫叮咬药方的描述,使模糊的情况更为具体化起来:“五岭之南不惟烟雾蒸湿,亦多毒蛇猛兽,故前贤有诗云:‘雾锁琼崖路,烟笼柳象州,巴蛇成队走,山象著群游。’又《编类集》及《岭外代答》《本草》诸书备言广郡多蛇虺、蜈蚣。愚既表出瘴疠论方,又不得不附治蛇虺螫蠚数方,以济人之缓急。”
这究竟是真实的所见,还是无端添加了想象的成分?其实并无不同,也许在中原人的心目中,南方边陲就是这样的烟瘴与猛禽怪兽横行的荒茫大地,从而架构出一个非我族类世界的“真实”图景。但若根据中医病理学分析,那些所谓的瘴病则可部分祛除神秘色彩,回归正常知识的渠道。隋代巢元方《重刊巢氏病源候论总论》所述甚详:
夫岭南青草、黄芒瘴,犹如岭北伤寒也。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故岭南从仲春迄仲夏,行青草三瘴;季夏迄孟冬,行黄芒瘴。量其用药体性,岭南伤寒,但节气多温,冷药小寒于岭北。时用热药,亦减其锱铢,三分去其二。但此病外候小迟,因经络之所传,与伤寒不异。然阴阳受病,会同表里,须明识患源,不得妄攻汤艾。假令宿患痼热,今得瘴毒,毒得热更烦,虽形候正盛,犹在于表,未入肠胃,不妨温而汗之。已入内者,不妨平而下之。假令本有冷,今得温瘴,虽暴壮热烦满,视寒正须温药汗之,汗之不歇,不妨寒药下之。夫下利治病等药在下品,药性凶毒,专主攻击,不可恒服,疾去即止。病若日数未入于内,不可预服利药,药尽胃虚,病必乘虚而进。此不可轻治。治之不差,成黄疸;黄疸不差,成尸疸。尸疸疾者,岭南中瘴气,土人连历不差,变成此病,不须治也。岭北客人,犹得斟酌救之。病前热而后寒者,发于阳;五热而恶寒者,发于阴。发于阳者,攻其外;发于阴者,攻其内。其一日、二日,瘴气在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痛恶寒,腰背强重。若寒气在表,发汗及针必愈。三日以上,气浮于上,填塞心胸,使头痛胸满而闷,宜以吐药,吐之必愈。五日以上,瘴气深结在脏腑,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或人得病久,方告医,医知病深,病已成结,非可发表解肌,所当问病之得病本末,投药可专依次第也。
巢氏将南方的瘴病与北方的伤寒看作同类型的疾病,只是病理不同,治疗方式不同而已。然而这种理性主义重视内在逻辑的思考多局限于十分狭小的医学圈子。尽管隋代已有医家达成这样的认识,但人们仍然热衷于对瘴的形象进行绘声绘色的文学描述,经过一些荒唐无稽的铺陈,甚至演绎为闻之而色变的闹剧。《新唐书·韦执宜传》记载唐顺宗时宰相韦执宜在朝做官时,竟然十分忌讳别人谈及岭南州县名称,去职方司观地图,“至岭南辄瞑目,命左右彻去” 。这样的态度与心理既可笑又可悲,物候惊惧的南方边陲产生如此巨大的隐喻力量,似乎已成不可磨灭之恐怖印象。
。这样的态度与心理既可笑又可悲,物候惊惧的南方边陲产生如此巨大的隐喻力量,似乎已成不可磨灭之恐怖印象。
不过,国家边陲的地理区域是随着中央王朝的势力扩张而不断推移的,根据瘴区范围的变化即可判断,最终在明清时期基本定型,“华夏边缘”遂得以正式确立。通过瘴气地理分布在王朝话语体系中变迁的考察,乃是探究“瘴”的本质内涵的一条重要途径。龚胜生运用长时段的视野对2 000年来中国“瘴”的地域范围进行了宏观的分析,经过详悉地考证指出,战国西汉时期以秦岭淮河为瘴域北界;隋唐五代以大巴山长江为瘴域北界,明清时期以南岭为瘴域北界。
中国古代瘴区变化呈现一种较为明朗的规律性,即自北向南推移,并逐渐缩减。其中固然有气候变迁的因素,但实际上还与中央王朝势力扩张的过程与程度大致吻合。秦以降,经过数个朝代的经营,“中国”之地不断扩大,原本的瘴区在先进华夏文明的影响下而“文明化”,因而“瘴”的北部边界也不断向南漂移。一直到宋代,南岭以南还被称之为“万里烟瘴之乡”。宋时的广东,瘴乡遍布,一些地区的瘴极为严重。
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广东瘴气所占之地已明显减少,虽然瘴仍有分布,但大部分府治或平原地带的县份已无瘴或少瘴。瘴病分布较集中的地带为广东北部、海南岛及与广西接壤的边远山区。其严重程度,纵向比较要低于前代唐宋,横向比较要低于临近的广西。 其原因可能在于“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疏豁。中州青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
其原因可能在于“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疏豁。中州青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 原本由广西与广东合称岭南的分野固然有行政划分的原因,也与广东经济、文化在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实情分不开,这时候广东的“瘴”印象得以大大改观。
原本由广西与广东合称岭南的分野固然有行政划分的原因,也与广东经济、文化在明清时期高度发展的实情分不开,这时候广东的“瘴”印象得以大大改观。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探讨了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从“仅仅为身体的疾病”转向道德、价值观评判的过程。她认为那些具有传染性的艾滋病、结核病,以及难以治愈的癌症等疾病代表着“恐惧”“肮脏”与“声名狼藉”等,反映了疾病背后的深层隐喻(Metaphor),即文化的、历史结构的、阶层的意识。![[美]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1DC1FE/2376555620141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119077-OLRkkjkU3yeicknFRRG0vXjfo9NV7cEF-0-2eff22024302269ee26dee18008b1044)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指出,疾病在未经医学“加工”之前,具有某种“原始”性质,所呈现的状态有如植物叶脉般的有序脉络。然而,一旦疾病所处的社会空间就变得越复杂,“变得越不自然”。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指出,疾病在未经医学“加工”之前,具有某种“原始”性质,所呈现的状态有如植物叶脉般的有序脉络。然而,一旦疾病所处的社会空间就变得越复杂,“变得越不自然”。![[法]米歇尔·福柯著:《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7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1DC1FE/237655562014128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0119077-OLRkkjkU3yeicknFRRG0vXjfo9NV7cEF-0-2eff22024302269ee26dee18008b1044) 很显然,福柯认为,社会空间的复杂程度决定了疾病的性质。桑塔格与福柯的观点为我们分析瘴气、瘴病提供了新的视野。
很显然,福柯认为,社会空间的复杂程度决定了疾病的性质。桑塔格与福柯的观点为我们分析瘴气、瘴病提供了新的视野。
古代中国对于南方边陲瘴气与瘴病的认识无疑也存在着一种隐喻,在自然属性的范畴中赋予社会化的观念形态。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有关瘴的描写大都是通过中原汉人的书写而呈现的,在他们的意识中,瘴气、瘴病与文化之间似乎有一种独特的反比关系,文化盛而瘴气少;反之,瘴气盛而文化落后,当然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中原文化。
北宋思想家李觏曾对赣南吉州与虔州文化、民风殊异的原因有过经典的评论,他认为:“南川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贡赋与其治讼,世以为剧,则其民甿众伙可识已。虽然,吉多君子,接瑞玉,登帝所者接迹,虔无有也。疑其 南越,袭瘴蛊余气,去京师愈远,风化之及者愈疏,乘其丰富以放于逸欲宜矣。”
南越,袭瘴蛊余气,去京师愈远,风化之及者愈疏,乘其丰富以放于逸欲宜矣。” 按照李觏的理解,虔州民风差可能是因为“
按照李觏的理解,虔州民风差可能是因为“ 南越,袭瘴蛊余气”,可见在他心目中瘴气之厉害,沾染与否能影响到社会的风气、习俗的教化。
南越,袭瘴蛊余气”,可见在他心目中瘴气之厉害,沾染与否能影响到社会的风气、习俗的教化。
瘴气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朝廷的边疆人事政策,清雍正帝在一条“圣训”中说:“朕思边省地方,或烟瘴难居,或苗蛮顽桀,官斯土者,与内地不同,是以边俸较腹俸之升迁为速耳。今太平日久,亦有烟瘴渐消、风俗渐淳之处,仍照旧例题补、升转,亦觉太滥。著九卿将各边俸之缺,或系瘴疠未除,宜令督抚等题补,或系风气已转,可照内地选用,一一分晰议奏。” 在这里,瘴疠与风气是等同的概念,雍正看来,消除了烟瘴或风气转化的边陲,基本与内地一体化了,官员任免就没必要再行特殊政策。这可能与当时大规模改土归流,国家力量进一步在边疆强化有一定关系。
在这里,瘴疠与风气是等同的概念,雍正看来,消除了烟瘴或风气转化的边陲,基本与内地一体化了,官员任免就没必要再行特殊政策。这可能与当时大规模改土归流,国家力量进一步在边疆强化有一定关系。
总而言之,上述内容说明“瘴”的存在与否和“文明”高低程度是关键性的指标。在这一话语中,瘴已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文化的观念。“瘴”的演变史,是一个由地理观念向文化观念转变的过程,折射出诸夏人士以自己的文化和地域为中心,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上对异地的想象与偏见。“瘴”之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分布范围的变迁,不全然属于生物与医学的认知范畴,也体现在中原文明与文化向周边传播和扩散,族裔向周边迁移的历史过程。 因此,“边陲”不仅是中原文明通过“瘴”意向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文化界定,也是一种政治的界定。由于桂西地区位处国家地理上的极边,从来都是烟瘴之地的核心区域,因而也是国家文化上的边陲和政治上的边陲。
因此,“边陲”不仅是中原文明通过“瘴”意向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文化界定,也是一种政治的界定。由于桂西地区位处国家地理上的极边,从来都是烟瘴之地的核心区域,因而也是国家文化上的边陲和政治上的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