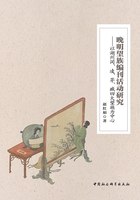
第四节 明清鼎革后望族经济衰弱
晚明商品经济繁荣而程朱理学控制减弱,由此带来了礼法观念与社会风俗的巨大变化。闵远庆《万历辛丑谱序》即谈到万历前后风气之变,曰:“今之不昔若也远。昔班在卑幼,习见诸祖父之御子姓也,拜则长揖而不答,揖则隅立以明尊,语及之则指行,……固云疏节,犹觇淳风。今不其然,钧礼矣,比肩矣,左右列主宾矣,动以号称,若他姓然矣。尊者日降而自抑,将卑者渐亢而自大目为故常,恬弗为意。稍或稜稜,辄反唇偶语,曰:‘胡迂也,胡倨也。’浸淫而喧哗于樽俎,恣睢于陆博,甚且立户分门,党同伐异,毁誉定于爱憎,淄渑混于舌端,名为宗枝,实同吴越。”[82]闵世魁《万历丁未谱引》也谈到当时社会风气的恶劣:“声华是兢,势利是炫,独为君子则忌之,蒙诟声则幸之。贫贱者凌之,患难者乘之,蔑而尊亲,弃而死丧。”[83]又《练溪文献·风俗》引嘉靖间唐枢论湖州风俗曰:“宏正以前颇存古意,尊长过之,必站立,贵贱不相干。嘉靖初,犹未尽漓。迩来人渐浇讹,恶少相诱讦讼,又有团局劫赌,子弟之幼稚者,往往入其计中……风俗之弊,莫可挽矣。”尊卑无序,立户分门,赌博诈骗,豪奢势利,礼崩乐坏的种种情形,在晚明时代都出现了。
伴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的轻商抑商观念逐渐发生动摇。晚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李贽曾大声责问:“商贾亦何可鄙之有?”[84]万历间《斗阳公(闵世魁)族谱凡例》曰:“士农工商,唯其材质所近,可力为也。”[85]湖州朱国祯所言“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86]、湖州唐枢所言“近惟以资财气力相雄长,而诗书故家,又复以和光同尘为尚”[87],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传统价值观在巨变。经商致富,在诗书故家看来,也不可耻,而晚明望族的商业编刊活动,除了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还必须有这种新的商业价值观开路。可以说,正是在晚明商业经济繁荣与社会价值观巨变的背景与前提下,晚明望族的商业编刊活动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然而如果望族编刊的经济基础不存在,即使商业价值观念不成障碍,其编刊事业也必然走向衰弱。入清后,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的商业编刊活动不仅繁荣不再,而且几乎可以说是销声匿迹。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鼎革之际,盗贼横起,房屋被焚,家族经济萧条。其中郑九是《晟舍镇志》中反复被提及、破坏力极大的一个匪盗。该志卷一《舆图》曰:“明季倭寇虽未至,而巨盗郑九率党羽焚掠,十室九空。”又,卷六《杂记》:“我里自明季郑九焚掠,房屋渐少。”卷一《河渠》:“闵吏部宅为巨寇郑九所焚。”卷一《衢巷》:“新开河东,前朝宅第连云,明季为巨寇郑九所毁,只存数宅。”卷一《桥梁》:“明季织里农人郑九为寇,聚众至晟焚掠”;“观音桥,明季桥北成市,接至笋店桥,后为郑九所毁。凌介禧诗:‘桥北昔闻市肆饶,可怜一炬土全焦。街衢泯灭无遗迹,隔水只存笋店桥。’”除了郑九,赤脚张三亦曾劫掠晟舍。该志卷六《杂记》曰:“明季赤脚张三,宋溇人,湖滨大盗也。张黄盖,竖五色旗,往来湖边,各溇无不被其荼毒,未几至晟里。”
在巨盗们的烧杀劫掠下,凌、闵二氏的刻板与书籍亦化为灰烬。如凌氏书林楼所藏刻板即毁于郑九之手。凌介禧诗曰:“观音桥北旧书林,郑九当年一炬侵。板莫重雕楼莫筑,半成禾亩半成荫。”[88]又,《凌氏著述叙录》曰:“闻明晟之村北多书肆,凌氏藏板皆在焉。鼎革时,为织里郑匪一炬,由是寥寥。今虽无力广购前本,重付诸梓,而篇目尚存,悉著于录。”[89]闵洪学之子闵亥生亦曾言:“乱后彼中(指滇南)刻板与予家藏本尽付劫灰。”[90]闵我备《闵遇五传》谈到《六书通》一书时曰:“今刻板毁于兵燹,其书亦仅有存者。”[91]
当然,凌、闵两望族经济上的衰弱还与鼎革之际家族中仕宦者相继死亡、政治势力削弱有关。凌族中显宦凌义渠闻知崇祯帝吊死煤山后,自缢殉国。其弟凌犀渠永明监国时为潮州知府,被叛将车任重所杀;石渠、熊渠亦“殉身王事”[92]。著名编刊家凌濛初于明亡这一年在徐州房村抵抗“流寇”,吐血而亡[93]。凌氏后人凌介禧诗曰:“五记登科命转穷,竹林何处器双忠。徐州判与潮州守,两殉封疆寇难中。”[94]所谓“双忠”即指凌濛初与凌犀渠,一殉于徐州通判任上,一殉于潮州知府任上。闵族中亦有闵洪得在四川抵抗张献忠而身亡,闵宾孟为中军都督府同知,国破殉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据《闵谱》,鼎革之际,闵氏族人为僧、未娶的情况很多,这也说明闵氏家族实力的衰落。
长兴臧氏在臧懋循孙辈经历明清易代,“维时两县鼎革,沧桑变无从,田园废尽,东山一墅且化为灰烬。期间流离播迁之事,不可胜数”[95]。《臧谱》卷五《太学生勇青臧公墓志铭》也谈到[96]:“鼎革兵燹之余,家业大半为山孽毁废。”茅氏在入清后亦繁华不再。施之桓《秋后渡花林》诗曰:“西江历乱藋芦风,借渡花林挠路穷。光禄池台寒树里,秘书粉腻夕阳中。砧催落叶孤村远,帆入深林一雁同。只有白华楼数卷,依稀犹认鲁王宫。”白华楼早已无存,董说清初所撰《楝花矶随笔》曰:“南浔报国寺后亦茅鹿门先生白华楼旧材。”[97]茅国缙万历时所购沈氏西楼在崇祯间即成废墟,清初时有书生过此楼,题诗云:“此第荣传三百年,身登金阙七人贤。当年第一城东号,今日萧然变海田。”[98]茅氏在双林的产业入清后亦零落无几,“今半植桑麻,惟茅家巷尚存花厅数椽而已”[99]。
就四大望族来看,茅氏家族的生命周期最为短暂。从嘉靖十七年(1538)茅坤中进士发家到万历间的极盛,再到1644年明清鼎革时衰落,最后到1661年因明史案发而败亡殆尽,前后仅一百二十余年。关于茅氏的盛衰过程与情形,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张履祥有很好的总结:
邑有茅氏,自鹿门以科名起家。兄弟三人,伯服贾善筹画,季力田精稼穑,鹿门其仲也,各以多财雄乡邑。广田畴,丰栋宇,多僮仆,其家风也。然治生有法,桑田畜养所出,恒有余饶。后人守之,世益其富,科名亦不绝四五世。间惟长支子姓渐少,家业浸薄;中支世业虽损,博学能文之士不乏也;少支方伯继起,子姓益繁于前,有光矣。族人仿效起家颇众,虽无显爵名贤,而阡陌衣冠,为百里著姓矣。二十年来败亡略尽,昔时堂户罔不邱墟,广陌无非萑苇。入其故里,惟族之贫者一二存焉。[100]
关于茅氏败亡原因,张氏亦有探讨。一是兼并土地,无厚泽于人,“窃谓占田之广,祖宗必以兼并得之,桑梓穷人不得耕其先畴者众矣,恶得无罪?”万历二十二年(1594),茅氏姻亲南浔董份家族因土地兼并而爆发民变,事件后来波及整个东南望族,作为巨富的茅氏当然也是被冲击者之一。二是遭遇罪刑,并涉庄廷鑨明史案,“又谓鹿门之后世有罪刑,近复史事被戮,本乎白华楼著述,好恶取舍徇于私,以是为余殃也”。所谓“有罪刑”概指茅坤长子翁积因违法瘐死,季子维因涉党祸而被人诬陷下狱,孙元仪因海运案而被追摄[101];所谓“史事被戮”即指茅坤孙元铭、曾孙次莱因名列庄氏《明史辑略》参订姓氏而获罪,导致家产被抄,家人或被杀,或远遁。张鉴曾引茅湘客《絮吴羹》曰:“元铭,字鼎叔,著名复社,以贡宰朝邑,为史祸株累,死者数人,子弟多远引。有兄之子名兆汾,字巨澜,号遁邱,实鹿门先生曾孙也。曾仕至参将,因弃为僧,名今渐,居匡庐,晚始改服归里。”[102]清《研堂见闻杂记》曰:“《明史》之狱,决于康熙二年之五月二十六日。得重辟者七十人,凌迟者十八人,茅氏一门得其七,当是鹿门后人。”
茅氏的败亡,除了晚明的民变和牵连罪刑、清初的文字狱,还有鼎革之际的匪盗劫掠和繁重赋税。茅氏所在练市附近有含山,《归安县志》卷四十九曰:“含山如盔形,其下常出强盗。若潘榜、徐龙、周道士,相继不绝。明末盗亦多,有富大、富二等,与泖湖诸贼相通,来至五里,乘大船,发号炮,鸣锣击鼓,声势最为可骇。”至于赋税的繁重,张履祥在谈到茅坤外甥顾氏时曾言:“为富大略慕效茅氏,豪横过之,辟土虽不及,占田已侈,科名世世相颉颃也。迹其败亡,与茅相先后,势则较重,岁负赋钱,男女桎梏相属也,幸者播逃,不可踪迹。”[103]
“至其盛也,丰阜乐逸”,“比其衰也,瓦砾之场,蒹葭之薮”[104],明清鼎革后望族经济衰落,其编刊活动失去财力支撑,繁荣不再,且从此一蹶不振。
[1] 朱闻:《练溪文献·风俗》,同治十一年本。
[2] 孙志熊:《菱湖镇志》卷十三引成化《重建真武祠记》,光绪十九年本。
[3] 孙志熊:《菱湖镇志》卷十三引万历《重修永宁禅院记》。
[4] 蔡蓉升、蔡蒙:《双林镇志》卷十八,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5] 蔡蓉升、蔡蒙:《双林镇志》卷三十一引嘉靖四十年沈桐《庆善庵新建观音楼序》。
[6] 蔡蓉升、蔡蒙:《双林镇志》卷三十一引万历陈所志《双林赋》。
[7]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引嘉靖茅坤《分署纪事本末序》。
[8]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
[9]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
[10]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与李汲泉中丞议海寇事宜书》,见张大芝、张梦新点校《茅坤集》(因频引此书,以下简称《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11] 钱尔复订正:《沈氏农书》,《丛书集成新编》第47册,第490页。
[12] 唐顺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五《茅处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铭》。按:《练溪文献·艺文志》题作《南溪茅处士妻李氏合葬墓志铭》。
[13]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亡弟双泉墓志铭》,见《茅坤集》,第682页。
[14] 屠隆:《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备兵大名道鹿门茅公行状》,见《茅坤集》,第1350页。
[15]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伯兄少溪公墓志铭》以及《耄年录》卷七《年谱》,《茅坤集》,第678、1244页。
[16] 学术界一般以为茅迁有三子,艮为其幼。然据茅坤《伯兄少溪公墓志铭》,茅迁临终时以财产“授少子大有,次者艮,次者乾,次则坤”,则迁有四子,其幼名大有。
[17] 茅氏种桑数十万株,那就非使用一定数量的雇工不可,特别是剪桑工、捉虫工等专门技术之工人。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5期。
[18] 当时“四十亩之家,百人而不得一也。其躬亲买置者,千人而不得一也”,见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八《与徐敬可》,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7页。
[19] 《茅坤集》,第681—682页。
[20]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七《祭亡弟参军文》,《茅坤集》,第763页。
[21]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四《敕赠亡室姚孺人墓志铭》,《茅坤集》,第701页。
[22] 屠隆:《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备兵大名道鹿门茅公行状》,《茅坤集》,第1356页。
[23] 《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与甥顾儆韦侍御书》,《茅坤集》,第307—309页。
[24] 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25] 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7页。
[26]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二《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志铭》,《茅坤集》,第668页。
[27] 朱闻:《练溪文献·艺文志》,同治十一年本。
[28] 双林在湖州城东五十四里,属归安县,崇祯时有人口一万六千余。东南至练市二十里,西北至晟舍十八里。花林在双林北。
[29] 祝世禄:《南宁判少溪茅公暨配郭安人墓志铭》言茅乾妻郭氏卒后,“蚕妾过而哭者千人”(《练溪文献·艺文志》)。笔者以为这些很可能是与茅氏在蚕桑丝织业方面有业务往来的农妇。
[30] 同治《练溪文献·乡村》“书街”条。
[31] 光绪《归安县志》卷三十六《文苑》。
[32]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四《敕赠亡室姚孺人墓志铭》,《茅坤集》,第701页。
[33] 《茅坤集》,第1369—1670页。
[34] 顺治间抄本《凌氏宗谱》卷七,以下简称“《顺治凌谱》”。
[35] 民国《双林镇志》卷四《街市》。
[36] 明知府沈熊之子沈环筑,在练市文星桥东。
[37] 周庆云:《南浔志》卷五十一《志余》引李乐《见闻杂记》。
[38] 朱彝尊:《明诗综》卷四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页。
[39] 就笔者现在掌握的研究资料来看,茅坤未有名镳的儿子。
[40] 陈尚古:《簪云楼杂说》,《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5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07页。
[41] 同治《晟舍镇志》卷一《舆图》。
[42] 《晟舍镇志》卷一《界域》。
[43] 《晟舍镇志》卷一《衢巷》。
[44] 见道光十三年(1833)刊《闵氏家乘》,以下简称“《闵谱》”。
[45] 《晟舍镇志》卷七《崇顺庵兰若记》。
[46] 《晟舍镇志》卷七《崇顺庵兰若记》。
[47] 《晟舍镇志》卷七《崇顺庵兰若记》。
[48] 同治《晟舍镇志》卷二《古迹》;乾隆《乌程县志》卷三《古迹》。
[49] 《闵谱》之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闵氏家乘序》。
[50] 《闵谱》之高淮《嘉靖辛丑谱序》。
[51] 《闵谱》之高淮《嘉靖辛丑谱序》。
[52] 《晟舍镇志》卷二《古迹》。
[53] 《晟舍镇志》卷二《古迹》。
[54] 郑龙采:《别驾初成公墓志铭》,见光绪甲辰重修《凌氏宗谱》(以下简称“《光绪凌谱》”)卷四《碑志》;或见《凌濛初考论》,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53页。
[55] 嘉庆乙丑刊《凌氏宗谱》(以下简称“《嘉庆凌谱》”)卷三《艺文录》。
[56] 《晟舍镇志》卷二《古迹》。
[57] 此园后归闵梦得,易名适园。闵梦得“致仕后,作归来堂,缭以周垣,佐以名花,为游息觞咏之所。登其石,则西北诸山环拱于石,俯瞰盘渚漾,波澜微动,荇藻交横,亦殊清旷幽雅”。见《晟舍镇志》卷二《古迹》。
[58] 《晟舍镇志》卷七文嘉《盟鸥馆记》。
[59] 《南音三籁·散曲下》梁伯龙《九疑山·寄情》后凌濛初按语,《凌濛初全集》第四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60] 凌迪知编:《国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4册,第595页。
[61] 凌迪知编:《国朝名公翰藻》卷五十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14册,第609页。
[62] 见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第7册所收凌濛初尺牍,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63] 见陈文新译注《日记四种》,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64] 《嘉庆凌谱》卷五。
[65] 《嘉庆凌谱》卷五。
[66] 当时同里董氏,田产数是数万。沈德符《敝帚斋余谈》:“时南浔董氏有田数万在吴江。”董嗣成《董礼部尺牍》卷上《与李二府》:“家下户田在吴江者,向有二万余亩。”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二:“(董份)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
[67] 明时双林街市繁华,不少望族在此经营店铺。如东迁沈楘在新街“构市廛,为收绢所”。楘,字文五,崇祯丙午举人,马腰南尚书沈演嗣子。见《双林镇志》卷四《街市》“新街”条。
[68] 《嘉庆凌谱》卷五。
[69] 光绪《长兴县志》卷一《镇市》。
[70] 臧懋循:《负苞堂文选》卷四,赵红娟点校《臧懋循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后文频引,仅注书名),第146页。
[71] 许次纾:《茶疏》,民国影印明宝颜堂秘笈本。
[72] 以上见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臧氏族谱》(以下简称《臧谱》)卷五刘宣《明故耕乐处士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铭》。
[73] 《臧谱》卷五张瑄《明故润庵处士臧公墓志铭》。
[74] 《臧谱》卷五顾应祥《明故龙南县知县北山臧君墓志铭》。
[75] 《臧谱》卷二《贡士臧恭乡贤录》。
[76] 《臧谱》卷一臧继芳《先妻吴安人行实》。
[77] 《臧谱》卷一臧照如《季父位宇公传》。
[78] 《臧谱》卷一臧炅如《明故上林丞位宇府君行状》。
[79] 《臧谱》卷一臧继芳《先妻吴安人行实》。
[80] 《臧谱》卷五沈圣岐《广西按察司佥事静涵臧公暨元配沈孺人合葬墓志铭》。
[81] 《臧谱》卷一臧照如《臧氏族谱序》。
[82] 《闵谱》第一册《序跋》。
[83] 《闵谱》第一册《序跋》。
[84] 李贽:《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刘幼生整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85] 《闵谱》第一册《序跋》。
[86]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
[87] 朱闻:《练溪文献·风俗》引。
[88] 见《晟舍镇志》卷二《园第》。
[89] 《嘉庆凌谱》之《著述录》。
[90] 《闵谱》之《著述录》闵洪学《滇南志》条引。
[91] 同治《晟舍镇志·艺文》。
[92] 《光绪凌谱》卷八。
[93] 《嘉庆凌谱》卷二《忠节录》曰:“闯贼之乱,凌氏死节之臣初成、忠介、龙翰三公,事业见于朝廷,忠义闻于天下,已堪俎豆不朽。他若石渠、熊渠二公,即忠介弟也,殉身王事,忠节亦不让前人。”初成即凌濛初,忠介即凌义渠,龙翰乃安徽歙县凌氏。
[94] 同治《晟舍镇志》卷五《凌犀渠传》。
[95] 《臧谱》卷五《明吏部文选司郎中醒涵臧公暨元配敕封吴氏合葬墓志铭》。醒涵乃臧懋中之子臧照如,所引之言乃臧照如卒后情形。
[96] 勇青乃臧照如子,名基辰,生于万历丙辰(1616),卒于康熙己未(1679)。
[97] 董说:《楝花矶随笔》,上海图书馆藏红印本。
[98] 见《练溪文献·园第》。
[99] 《双林镇志》卷四《街市》“赛双林”条。
[100] 《归安县志》卷四十九《杂识》引张履祥《杨园先生集》。
[101] 所谓海运案被追摄,是指崇祯间茅元仪为权奸所中,借口昔日所募楼船沉海之事,被“从戍所逮回,代人偿海运”,见茅元仪《三戍丛谈》卷三。等到“奔走竣其事”,“家田庐已尽,独留‘又岘’”,见茅元仪《石民又岘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102] 周庆云:《南浔志》卷五十七《志余》引张鉴《蝇须馆诗话》。
[103]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八《近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37页。
[104]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八《近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