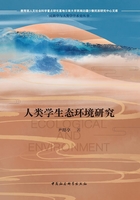
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003年6月19日是宋蜀华先生80 华诞。五十多年来,先生教书育人,著述颇丰,深受学界景仰。当我们重温先生的学说,可知在他关注的诸多研究对象中,“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占有重要的位置。2002年7月,中国民族学学会在湖北恩施市召开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作为会长的宋先生在开幕词中又再一次讲了“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指出“这是民族学者应当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1]。遵照宋先生的教导,本人欲谈谈学习生态人类学的一些体会和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情况,以表达对先生华诞的良好祝愿。
一 国外文化生态理论的回顾
关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早期的理论是“环境决定论”。所谓“环境决定论”,是指以地理环境为唯一因素解释社会文化差异的认识论。环境决定论的产生可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17、18 世纪又受到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guien, 1689—1755)和英国的巴克尔(Henry Thomes Buskle, 1821—1862)的进一步宣扬,[2] 以致这一主要以气候因素解释国家、人种和民族优劣的论调得以盛行一时。
说到环境决定论,通常也会把德国著名学者F.拉策尔(F.Ratzel,1844—1904)作为其代表人物。拉策尔深受达尔文(Charles Rober Darwin, 1809—1882)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3]。然而,综观拉策尔的学说,如果全部贴上“决定论”的标签的话,那就错了。[4] 拉策尔其实是一位在人文地理学和民族学两个学科内承前启后、具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他的大著《民族学》是按照地理分区记述民族文化最早而科学的世界民族志;其另一部名著《人类地理学》则将业已分化的地理学和民族学再度结合,通过考察人种、民族和文化“在哪里”(分布),“从哪里来”(传播与模仿),从而进一步探索民族及其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5]拉策尔的地理分区、民族文化分布和传播的理论,对后来的地理学和人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拉策尔之后,人类学界仍然保持着较强的人文地理学的倾向。20世纪前期的美国人类学,在博厄斯所倡导的注重地区调查和实证研究的学风的培养下,很多学者开展了对文化要素分布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以探讨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由威斯勒(O.Wussler, 1870—1943)提倡,继而又由克鲁伯(Kroeber, Alfred Louis, 1876—1960)发展了的文化区(Culture Area)概念,大大推动了民族文化地域研究的发展。威斯勒在其著作《美洲印第安人》(1922年)中,把新大陆原住民的文化设定为15个文化区域,他认为“赋予文化地域特性的因素是经济形态,尤其是食物获取手段,即表现于部落生活中最显著的地域特性乃是食物的获取”[6]。克鲁伯亦非常重视与自然环境差异相对应而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差异,他欲从整体上把握以最能体现自然环境差异、作为人们直接或间接生存资料的植被为基础的文化,怎样具有对应于地域的不同性质。据此,他在其名著《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和自然区域》(1939年)一书中,将北美洲分为6个大文化区、21个小文化区。[7]
威斯勒和克鲁伯有关“文化区域”的研究,着眼于与自然环境差异相对应的文化差异,并指出不同的文化区即不同的地域文化乃是经济形态和以作为生存资料的植被为基础的文化,这显然是远远高明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真知灼见,抓住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纽带,可以说已经具有生态学的内涵了。
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即从人类地理学的模式跨到生态学的视野,斯图尔德(Steward, J.H., 1902—1972)应是开创者和奠基者。前文说过,拉策尔倡导了民族及文化的地理分布和传播的研究,威斯勒和克鲁伯创立了进一步研究文化分布及其地域特征的“文化区域”概念,并注意到了对应于自然环境的文化层面。那么,为什么人类的某些文化总是因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差异,并且表现出密切的对应关系呢?威斯勒和克鲁伯对此没有做出解释。斯图尔德的贡献就在于他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生计为中心的文化的多样性,其实就是人类适应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的结果。“适应”是生态学的核心概念。从人类学的角度讲,适应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承认自然环境对于生物属性的人类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社会的文化的人类对于自然环境所具有的超常的认知、利用甚至改造能力。适应犹如通往文化殿堂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便获得了阐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阐释文化及其演化的一个有效的视角和途径。斯图尔德的学说之所以被视为人类学独树一帜的方法论,[8] 而且被称为“跨学科的文化生态学”,就在于他把生态学的“适应”概念引入了人类学,并运用于文化及其演化的阐释。
20世纪中期,人类学范畴或与人类学有密切关系的生态学取向研究不断涌现,并产生了若干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又有不同学识背景的边缘学科,如生态人类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这一学科领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生态人类学属人类学门类,是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人类学以人类的适应——主要是文化适应,也包括生理适应——为研究对象,借鉴应用生态系统的概念,在系统的结构和运动中具体考察各种文化、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以发掘和整理作为人类适应的知识和行为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进行生态学角度的文化及其演化的阐释。
人类生态学是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医学、遗传学等学科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人类生态学也以人类的适应为研究对象,然而它所关注的却主要是人类机体和生理的适应,进化以及当代的环境问题。其研究领域包括人口、遗传、体质、营养、疾病、生计、资源利用、社会发展等与环境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在一些国家,也将古人类进化的研究纳入人类生态学的范畴。
民族生态学来源于民族学、植物学和生态学的相互渗透。民族生态学关心土著民族对其生境“认知”的传统知识,动植物资源的分类知识和利用方式是其考察的核心。参照现代动物学、植物学和生态学的科学体系,去比较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从而达到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保护和利用的目的,这就是民族生态学的研究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人类学的家族中又多了一个生态学的方向——环境人类学。日本学者绫部恒雄于2002年主编的《文化人类学最新术语100》一书,选录了近15年来人类学新生的应用率高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的100个术语,其中便有“环境人类学”条目。该条目把环境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以下6点:(1)人类进化和适应;(2)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3)自然认知和民俗分类;(4)自然和世界观、信仰体系;(5)围绕共有资源的人类学视点;(6)政策提案的努力等。[9]
从环境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难看出,它与人类生态学有所交叉,而与生态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却很难截然区分。那么,为什么在同一研究领域会不断出现新的学科术语呢?原因便在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研究空间的广阔和内容的丰富,它蕴藏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众多学科的资源,吸引了多学科学者的关注和参与。不同的学识背景和方法对学术资源不同的发掘和利用,自然会产生多样的视角和观点。
2000年10月,“云南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和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共同举办了国际学术盛会——“2000年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国际研讨会”。百余位活跃于当今国际文化生态研究舞台上的专家学者会集云南,进行了十余天的讨论和考察。大会收到的一百多篇论文和热烈的会议发言主要集中于以下8个专题:(1)自然资源·地方性社区;(2)地方性知识·宇宙观;(3)农业生物多样性;(4)社区基本资源管理;(5)全球化·市场·生物多样性;(6)生态旅游;(7)不同文化交流·参与性;(8)本土资源权利。这8个专题基本上反映了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生态学研究的前沿和趋势,那就是多学科的进一步交叉、融合,社区资源管理利用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以及文化、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10]
二 国内研究概况
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和人文地理学都是20世纪早期从西方引入的学科。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已出现功能和历史学多种学派的分化,[11] 然而却少见人类地理学倾向的专门研究。在人文地理学方面,一批学成归国的地理学者编著和翻译了大量有关人文地理学的著作,[12] 但是人类地理和民族地理的研究还很少。20世纪50年代之后,两个学科均受到冲击。人文地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成为禁区;民族学同样遭到取消的命运。然而,由于国家面临着少数民族和边疆稳定的问题,所以民族调查研究并没有停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由国家民委主持编写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学者长期深入田野调查研究的成果。
综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调查报告,几乎每篇报告都有民族分布、村寨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以及生计方式的记述。有些报告,例如黎族、彝族、佤族、傣族、独龙族、布朗族、景颇族等民族的自然环境与生计方式的调查,可以说是相当的详细,大都成为不可再次搜集的珍贵史料。不过,由于当时的调查完全依据社会形态进化的理论,所以其局限性和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社会形态进化的理论,各民族的食物获取方式,即生计形态的差异并非是不同民族与不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亦即社会发展阶段的表现,这种观点与生态学的观点显然大相径庭了。
在进化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同角度的文化阐释显然是不合时宜而受到排斥的。尽管如此,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止,1958年林耀华先生与苏联民族学家切博克沙罗夫教授合作编写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便是当时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论文里,作者明确指出:“东亚各族的各个经济文化类型(全世界范围也如此)反映着它们处在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13] 根据这样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按照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划分具体的经济文化类型,[14] 并就此展开讨论。林耀华先生的经济文化类型研究与美国的文化区域学派和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显然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林先生在重视自然环境所影响的“横向”的经济文化类型的同时,还强调“各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纵向”的“采集、渔猎,锄耕农业,犁耕农业”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的进化,[15] 形成了环境影响论和社会进化论相结合的阐述方式。
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人类学领域的生态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活跃的时期。先是《民族译丛》等杂志陆续刊登了有关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地理民族学、民族地理学以及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翻译和探讨的文章。此后,在杨堃、庄锡昌、孙志民、童恩正、林耀华、陈国强、黄淑娉、龚佩华、宋蜀华、白振声、和少英、庄孔韶等编著和编译的人类学和民族学通论、概论以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著作中,都有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的专章、专节的介绍和论述。在老一辈的民族学家当中,宋蜀华先生对生态的研究尤为关注。1993年,宋先生撰文介绍生态民族学;[16] 1996 年,宋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发表了名为“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论文,论述了生态环境与民族发展繁荣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根据中国历史文化生态的状况,划分出8个大的生态文化区,并强调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和调适。[17]
北京、贵州、湖南、新疆、福建等地的一些学者,在借鉴和吸取国外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锐意探索,致力于本土田野的调查,也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论文和专著。云南由于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环境多样性以及优良的学术研究传统,因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在生态学方面,一批中青年学者开拓了人文生态的研究,其代表人物云南大学生化学院周鸿教授通过长期潜心钻研,先后出版了《生态学的归宿——人类生态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文明的生态学透视——绿色文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人类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多部专著和许多论文,对我国人类生态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植物学方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裴盛基研究员,于1982年在我国大陆首倡属于民族生态学范畴而又自成体系的民族植物学。昆明植物所于1987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此后又设置了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培养了一批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在全国举办了与民族植物学相关的十多个国际会议和培训班,带动了西藏、四川、内蒙古、新疆、贵州等省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开展。迄今为止,裴和他的同事们已编写出版《民族植物学手册》(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应用民族植物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等专著十余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五百余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9年和2000年,“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和“2000年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国际研讨会”在昆明召开;2000年,裴盛基当选为国际民族植物学协会主席。不言而喻,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影响日益显著,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近年来,云南大学充分发挥民族学重点学科的优势,对相关学科进行整合,开设了生态人类学、人类生态学、体质人类学、民族植物学、人类遗传基因、人文地理学等课程,并在硕士、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中设立了生态人类学、人类生态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向,培养了一批跨学科的专业人才,组织和实施了若干重大项目,现已成为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和相关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镇。
三 拓展人类学生态研究的领域
早期人类学中的生态研究在于探索将其作为文化及其变迁的一种阐释途径的可能性。当代的研究,除了保持其文化阐释功能之外,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回答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生态问题,还必须有所发展、有所开拓。下面笔者将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一谈生态人类学今后应加强研究的几个方向。
首先谈当代适应的研究。如前所述,人类学的生态研究,目前已经有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和环境人类学等分支,今后随着各分支学科的逐步完善,不排除还将产生新的边缘交叉方向。然而,不管怎样分化,不管取向如何,既然是生态学的研究,就离不开最基本的立足点,那就是适应。适应的研究永远是生态研究的核心,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适应是一个变化丰富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类与环境,应具有不同的适应方式和内涵。作为当代人类适应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给予充分注意的。
首先,绝大多数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从单纯的自然环境变成了复杂的自然、社会环境。在早期生态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中,许多土著民族的生态环境基本上是封闭的自然环境。例如,因纽特人生存的北极地带、安第斯山人和西藏人的高寒山原、努尔人等的热带干草原和沙漠、美洲中南部的印第安人和非洲俾格米人等的热带雨林,都是与外界交往很少、十分封闭的自然环境。而在封闭的、单纯的自然环境中的人类适应,包括生理、认知和行为,均非常明显地表现着比较直接和突出的环境特征。例如,分布在靠近北极地带的因纽特人,在生理上,他们的新陈代谢循环率比温带与热带人大约快60%,这就使得他们的身体和手足能对严寒侵袭产生快速反应,即使其身体的某个部位(如脸、手)短暂地暴露于外,也不会被冻伤;在认知方面,他们具有丰富的关于冰、雪知识,因而能够避免频繁发生的冰雪灾害;在生计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他们采取不稳定的迁徙生活方式,那是因为必须追寻驯鹿并随季节沿河岸和海岸捕捞鱼、海豹和海象。他们一直保持着在捕捞海豹的季节进行合作和分肉的做法,这是增加个体家庭生存机会的合理手段。此外,他们居住在草皮屋和雪屋,穿着鱼皮和兽皮衣服,有效抵御了严寒;他们信奉萨满教,在冬季有举行盛宴仪式、性交换等习俗,这些都与人在严寒郁闷的状况下需要情绪宣泄和减轻精神压力有关。他们还有延长哺乳期、堕胎和杀婴的习俗,这种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人口结构的方法,与生存资源的稀少和波动不无关系。[18] 像因纽特人这样独特的生境及其适应,便是早期生态人类学理想的、典型的研究对象。
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欲寻找与世隔绝、完全封闭的部落和生境,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毕竟越来越少了。我们面对的大多是因国家、移民、市场、现代科技等因素介入之后变化了的原住民和生境。也就是说,当代生态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已非单纯的自然环境及其适应,而是复杂的生境和适应了。对于这种情况,也许以当代旅游研究为例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最近几年,我们尝试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旅游,其焦点是“旅游生境与文化适应”。所谓“旅游生境”,是指开展旅游活动具体的乡村或社区环境,该环境必须具备自然或人文旅游资源,并且具备开展旅游活动所必需的各种服务设施和条件,而更为关键的是“游客”,它是旅游生境中最重要的“环境要素”。一个村寨或一个社区,从以单纯依赖自然环境的生计为生的生境变化为旅游生境,人们的适应必然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变化将首先发生于因游客的进入而产生资源观念的转变:可供生存的资源不仅仅是森林中采集狩猎的植物和动物、湖泊河流中可捕捞的鱼虾、草原中可放牧的牲畜以及农田中的作物,森林、湖泊河流、草原、农田本身以及过去毫无食物产出的雪山、峡谷、海岸、沙丘,等等,也都会令人难以置信地转变成为可供出售的“景观”资源,而且价值巨大。不仅如此,传统民居、服饰、饮食、工艺、歌舞、礼俗、节日、仪式等土著文化,也因为游客娱乐和体验的需要而具有商品的意义。市场的发展和游客的需求,极大地激发了当地人的活力,各种适应行为应运而生。如我们重点调查的云南省丘北县仙人洞村,10年前还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十分封闭的村庄,是旅游揭去了它的面纱,使外界看到了它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淳厚的撒尼人及其古朴的文化,同时也使村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且迅速认识了旅游业和游客。于是,导游和划船业在村中悄然兴起,神山、神洞、神像等作为“景点”开发热闹起来。村头开辟修建了歌舞演出和祭祀的场地,传统自娱自乐的篝火晚会成为招揽游客的重要项目。曾经消失了的传统毕摩祭祀仪式复活了,在原有火把节的基础上又创造了“赛装节”“荷花节”等新颖的节日,一些村民把老民居改建成家庭旅馆,“农家乐”的经营活动替代了古老的打鱼种田……[19]这是何等惊人的文化变迁!这种变迁充满活力和生机,然而也存在着不少消极和危险。它极大地丰富了当代适应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开拓。
其次,谈谈传统知识研究的意义。生态人类学关注生境和适应的变化,同时重视传统知识。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中,具有丰富、独特的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观念、伦理、法规和合理利用管理自然资源的经验、措施和技术等,它们是各民族对其生境长期适应的智慧结晶,不仅具有历史、文化的价值,而且对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迅速消亡的情况下,人们对其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仍然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蔑视的态度,甚至总是希望尽快将其淘汰,殊不知这是非常无知和愚蠢的。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从事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研究,历时十余年,观点和结论引发了不少争议,原因何在?归根到底,就在于对传统知识认识的分歧。众所周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凡涉及中国西南山地民族的调查报告都毫无例外地将刀耕火种定性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或“原始社会习俗”。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环境问题才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于是,刀耕火种又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因而遭到社会和学术界的猛烈批评和指责,甚至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也对其表示过关切。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说它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话,那么,当时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已经近半个世纪,为什么它却依然延续而屡禁不止呢?如果说它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么,为什么刀耕火种盛行了几千年并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像西双版纳那样的“刀耕火种王国”的森林覆盖率却依然高达60%以上呢?显然,这两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于是,笔者试图摆脱当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进化论的束缚,同时向极具惯性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来自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偏激的自然保护主义提出挑战,希望用“适应”和“传统知识”的观点去认识和解释刀耕火种。这在现在看来应是一种极其正常的探索途径,而在当时却是“离经叛道”的“歪理邪说”,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风险。
回想当年之所以涉足“禁区”,多半是因为田野发现的激励。在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知识库里,接触到他们长期积累的关于天象、地理、植物、动物等方面丰富的知识;了解到他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分类利用的方式;发现了他们对于森林土地资源进行用养结合的轮歇耕种系统;看到了他们因地制宜的各种耕作技术;整理了他们所驯化、引种的大量栽培作物和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保护地力所创造的混作、间作、轮作和粮林轮种等经验和技术;理解了他们将采集、狩猎、农业有机地进行结合,以充分获取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学习了他们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土地分配及管理等种种法规。此外,还涉及他们如何凭借世俗的力量和长者的权威,以及种种宗教仪式来维护社会和生产的正常运行、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等等。调查结果充分说明,刀耕火种并不能简单地以“原始社会生产力”和“原始社会习俗”来定义,也不能轻率地将其作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来批判,它其实是人类对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是一个有着独特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的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份数千年来不断创造、积累的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20] 今天我们研究、整理和发掘像刀耕火种这样的传统知识和文化遗产,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更重要的是于现实有益。别的不说,仅就刀耕火种的粮林轮作方式和技术而言,就值得继承和发展,因为这种方式和技术的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利用的价值是现代化学农业所远远不可相比的。
最后,谈谈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应用。生态人类学研究是文化阐释的一种途径,而在当代文化多样性迅速消失和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生态人类学关于适应和传统知识等的研究,直接关乎以下重大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如何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各少数民族传统生计的基础上,建造新型的生计模式以摆脱贫困、奔小康?如何谋求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的探索,更需要通过应用和实践以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常常感到人类学边缘化的寂寞,并不时为本学科和学者所处的非主流地位而感到尴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状况,笔者认为,其原因并不在于人类学学科本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应用研究的薄弱。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巨大发展机遇的时代,学术不仅要重视理论的探索和追求,而且还应努力“转化”研究成果,使之与时代的要求紧密地结合,从而体现学科和学者的价值。我们知道,早期人类学的发展就与西方国家推行的殖民主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等地区的研究以及美国对日本的研究等,也多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目前,在一些国家,人类学学者参与国家的民族事务、文化事业、资源利用、社区发展、环境保护、旅游规划等的咨询、决策和管理,已经非常普遍。中国人类学其实不乏“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费孝通先生和宋蜀华先生等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积极开展应用研究,也将有力地推进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最近5 年,我们在应用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997年,经过多年的思索,我们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构想,这是针对当代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迅速消亡、持续发展面临危机、急需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一重大问题而设计的一个应用性课题。什么是“民族文化生态村”?简而言之,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力求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发展模式。关于“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因篇幅所限,此不赘述,笔者在《民族文化生态村——云南试点报告》[21] 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阐释。
结束语
以上粗略地回顾了国内外人类学生态研究的概况,并介绍了我们多年来在该领域的思考和探索。客观而言,我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尚起步不远,同时还面临着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艰巨任务。作为承前启后的中年一代学人,我们将在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有所建树,有所作为。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编《中国民族学纵横》,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中国民族学会》,《民族学通讯》2002年第137期。
[2]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3]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4][英]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5页。
[5][日]今西锦司等编著:《民族地理》上卷,东京朝仓书店1965年版,第11—17页。
[6][日]今西锦司等编著:《民族地理》上卷,东京朝仓书店1965年版,第18—20页。
[7][日]今西锦司等编著:《民族地理》上卷,东京朝仓书店1965年版,第12—21页。
[8]黄应贵主编:《见证与诠释——当代人类学家》,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180页。
[9][日]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最新术语100》,东京弘文堂2002年版,第46—47页。
[11]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160页。
[12]张文奎编著:《文化地理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7页。
[13]林耀华:《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载《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4]林耀华:《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载《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15]林耀华:《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载《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6]宋蜀华:《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载《民族学研究》第十二辑,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17]宋蜀华:《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8]Emilo F.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Westview Press, 2000, ed., pp.114-135.
[19]尹绍亭主编:《民族文化生态村——云南试点报告》,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8—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