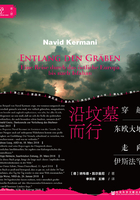
第二天 从柏林到布雷斯劳
在罗莎·卢森堡广场上,在民族剧院的屋顶,红彤彤地亮着三个巨大的字母“OST”(东)。光是这几个字母便已经体现出重新统一后的柏林,甚至是统一后的欧洲的一种姿态,不,是一个矛盾:“东”。过去的20年里,许多大型的,因其时长(5、6、7个小时)而耗尽人体力的舞台演出都是改编自俄国小说。系列讨论的题目叫“资本主义与抑郁症”,后来又叫“政治与犯罪”。市政府刚刚做出决定,要让这个德国最重要的话剧剧院成为国际节日文艺活动的多媒体演出场地,场上主要说英语。当然也会有涉及移民话题的演出。
开往火车总站的出租车路过了一个塑料立方体,其大小超过了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其他所有建筑:大教堂、大学、歌剧院、勃兰登堡门。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这遮挡物背后,工人们在一砖一瓦地重建霍亨索伦宫殿的华丽外墙,就仿佛可以如此来修正历史。覆盖住楼正面的广告牌号召人们“有雄心,做更大”。广告代理商是不是仔细考虑了一番才挑选了这张海报?海报上恰恰颠覆性地展示了一片被智能手机镜头框起来的风景,一支笔在上面为现实风景添加内容。未来,这里恰恰要通过对普鲁士宏伟景观的模拟来展示世界文化。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得到。一个楼层已经改作他用,更恰当地用来呈现本国本地历史了。现在只要把1848年革命失败后象征国王允诺的上帝之宽恕的黄金十字架重新安放到宫殿上,让它像殖民藏品中的一面旗帜一样高高耸立,那么世故圆滑的面目就要完全展示出来了。
我在帝国大厦——它的穹顶在柏林墙倒之后也重建了,但是没有拷贝历史原样——下了出租车。因为早到了几分钟,所以我没有拖着行李箱往右去火车总站,而是往左去了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这居于市中心的位置和纪念碑的尺度越是显得政治正确,这个混凝土方块组成的可进入的地段就越是让我感到不幸,因为这地形是要制造出从来不可能有的感情共鸣。我现在第一次从北边走近了纪念碑,不由得吃了一惊,这些高耸的石块形成了一个黑灰色的坟墓山丘,在这山丘背后动物花园[1]便成了一座墓园,而周围的办公楼则变成了行政楼群,其线条和颜色都与混凝土石块呼应。勃兰登堡门突然之间化为了一座不可随意出入的园区大门。因为屠犹罪行已经超过了想象力,因而目光所及,罪行趋于抽象化,这样的凝望让我与纪念碑有了几分钟长的和解。但是当我随后走到方块之间时,我立刻又感到惊愕。它们耸立得越高,城市越显得疏离,我越是如其所愿地感到迷失,我就越厌恶这种廉价的效果。我觉得这特意做得不平整的水泥地面实在粗暴,它据说模拟了受害者颠沛不安的人生感受,但对于拉着行李箱的人来说却是可想见的最庸俗的阻碍。相比之下,通往地下“紧急出口”的陡峭阶梯旁的安全围栏,在我看来更实在一点。
往东边去的火车总是这么空吗?要承认这一点比较难为情:我还从没去过波兰。在德国西部腹地出生长大的我们,眼睛总是看向法国、意大利、美国;就算是(中东意义的)东方,我们了解得都比我们自己国家的东部更多。现在火车开过了奥得河,这看起来还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河,没有被修坏或改直,河岸自在蜿蜒。距离到达波兰还有不到30秒,东方已经像安杰·史达休克[2](Andrzej Stasiuk)书中所写那样显出了古朴的样貌。不过,当然了,板式建筑也马上出现了。30秒之后。
在波兹南我差点错过了去布雷斯劳[3](Breslau)的列车,因为我虽然有了那么多旅行经验,可还是在车站晕头转向,出示车票问路时又听不懂任何人的回答。然后我还在火车站的面包店旁边站了一会儿:如果有什么是让我觉得有典型德国特色的,那就是全麦面包了。现在我却发觉波兰人或者至少波兹南人把面包烤得和德国人一样黑,在饮食方面德国更属于东欧而非西欧,更不用说南欧了,南欧是在最近几十年里才进军德国厨房的。将欧洲大陆历史性地分开的,不是白香肠界线,而是白面包界线。在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是和波兰、捷克甚至匈牙利一起理所当然地被看作中欧的,德国知识分子也都注重解释,是什么将他们的国家与西方分隔开。当我终于坐到火车里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连头等座都没有空位了,似乎波兰人都只在自己国家内部出行。
在布雷斯劳,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4]中心的主任,历史学家柯西茨斯多夫·鲁赫尼维奇(Krzysztof Ruchniewicz)告诉我,赫尔穆特·科尔[5](Helmut Kohl)在波兰远比我那一代为和平呐喊的西德人的榜样人物受欢迎。是,勃兰特认可了奥得河-尼斯河边界[6],但是他后来没有支持反共产主义的波兰反对派,在1985年访问波兰的时候也拒绝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莱赫·瓦文萨[7](Lech Wałęsa)见面。如果我在我们所坐的咖啡馆旁边这个紧邻犹太教堂的广场上四处打听一下,几乎不会有人知道那位联邦总理的名字,这还都是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而且连1970年那次下跪也几乎没有哪个波兰人听说过,鲁赫尼维奇说道;下跪的照片仅在一家犹太人的报纸上出现过一次,之后再发表的时候也都是经过修改或者截去一半了的——没有膝盖的勃兰特。
而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在往西几公里的地方长大的人的脑子里从未有过的事实是,所有布雷斯劳人,无一例外,都有名声不好的“移民背景”;1945年发生过一次彻底的居民交换,所有60万德国人都被赶走,其实还要更多,因为西里西亚被看作德国的防空之地,许多难民从西边逃了过来在这儿居住。犹太人被驱逐过两次,不对,三次:第一次是被德国人硬塞进去往奥斯维辛、特雷津、马伊达内克[8]的火车里;少数在布雷斯劳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战后作为德国人被赶走了;最后一批人本来是和其他波兰人一起安置到城里来的,他们被发现是犹太人,又被驱逐走了。对这一切,我们都只模模糊糊地知道零星半点,因为我们在学校的课上,如果提到这个不再属于德国的地区,也只是羞愧地说了几句。不过即使是在波兰本国,鲁赫尼维奇说,大家也只是按统一的模式来回忆自己的过去,都把波兰人仅仅看作受害者。尤其是新一届保守政府绝口不提任何对犹太人的驱逐,更不用说对德国人的驱逐了。
我试着想象波兰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今天的乌克兰被驱逐回来的——是如何进驻布雷斯劳的;他们如何走入被匆匆遗弃的德国人的住宅,打开衣柜和抽屉;鞋匠如何四下寻找制鞋工坊;医生如何寻觅合适的诊所;学校里也许还挂着上一个班的素描画、管家的大褂、校长的带有德国标签的礼帽——这个礼帽新校长戴着合不合适?人们会以为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所有居民,就连带着失去了它的历史,生活根本不能继续下去,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布雷斯劳看起来就像从没有住过其他人一样。
柯西茨斯多夫·鲁赫尼维奇讲述道,有一次,被驱逐的德国人来到了哈珀施韦尔特[9]附近他妻子的村庄里,子孙众多的一大家子或者也可能是好几家人坐着公交车。德国的祖母下车来,顽固地打听房产的价格,每一次都被她的几个女儿拉了回去,最后被推挤上了车。公交车绕了一个弯,又在鲁赫尼维奇的岳父母家门口停下了。有人从司机座的小门递过来一份小礼物,一小包咖啡,然后车子开走了。“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维利·勃兰特中心主任说,“特别怪异:我们肯定也给了他们什么,我们问自己——可是给了什么呢?”
当我晚上给安德雷亚斯·卡尔比茨发邮件,感谢他对我的友好招待的时候,我——老实说有点儿自作聪明地指指点点,但是有时候手指动起来比理智要快——写道:“我从布雷斯劳发去问候,不是面向世界的开放,而是民族主义让这儿不再有德国人居住。”
[1] 位于柏林城市西边的一座大型公园,原来是王室的狩猎场,故有此名。
[2] 波兰当代作家,出生于1960年,以反映东欧现状的游记出名。
[3] 即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ław,波兰第四大城,二战以前是德国城市,德语名称为Breslau。
[4] 德国当代著名政治家,社会民主党领袖,曾任西德总理,他在华沙的犹太起义纪念碑前下跪的行为举世闻名。
[5] 德国当代著名政治家,基民盟领袖,曾任西德及统一后德国总理,在任期间东西德合并。
[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将德国与波兰的边界西移,抵达奥得河与尼斯河。德国就此失去包括但泽和东普鲁士大片领土。苏军随后将德国居民驱逐。东德首先承认该边界。西德政府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影响下在1970年与苏联、波兰签署条约,承认这条边界。
[7] 波兰当代政治家,人权运动家,198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0年出任波兰首届民选总统。
[8] 这三个都是纳粹德国建立的集中营。
[9] 即波兰城市贝斯奇察·克沃兹卡(Bystrzyca Kłodzka),Habelschwerdt是原德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