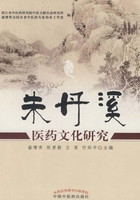
援儒入医 相得益彰——丹溪医学的哲学思想
朱丹溪是杰出的医学家,也是重要的理学学者,理学和医学,实已成为丹溪思想中浑然为一的整体。黄宗羲等人的《宋元学案》列丹溪于“北山四先生学案”,当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是朱熹四传弟子许谦的学生。
许谦,字益之,婺州金华人,学者称白云先生。许谦及其上三代宗师:何基、王柏、金履祥,在金华地区递相授受朱熹理学,是金华理学的主要传人,史称“金华四先生”,亦称“北山四先生”。《元史》载,“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嫡。”所以,元代金华理学号称朱学嫡脉,而许谦被称为金华理学大师。卒后十年之至正七年(1347),赐谥曰文懿;所著有《读书丛说》《读四书丛说》《白云集》及《诗集传名物钞》等。许为教凡四十年,时人黄缙谓其“出于三先生之乡,克任其承传之重。三先生之学卒以大显于世,然则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大至许公而益尊”,对程朱理学的发扬和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丹溪师事许谦,确是其人生的转折点。许谦为之“开明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丹溪则“日有所悟,心扃融廓”,由此苦读默察,见诸实践,严辨确守理欲诚伪之消长。“如是者数年,而其学坚定矣。”《宋元学案》引宋濂说,认为“其学以躬行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为礼乐之原,积养之久,内外一致”。自此之后,丹溪处事行世,待人接物,著书立说,率以理为宗;理学亦成为丹溪学术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丹溪援理入医,影响深远,竟由此而形成中国医学史上哲学思想进入医学领域的第二次高潮。
(一)“格物致知”的医学理论思维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朱熹理学的中心内容之一。何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何谓致知?即“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也就是通过辨察形而下的事事物物,来认识形而上的天理,即是物中见理,由寡而多地推展扩充知识。许谦继承发挥了朱熹的这一学说,更强调心的认识作用,“格物之理,所以推知我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去穷究,格来格去,忽然贯通……事虽万殊,理只是一,晓理只在此事如此,便晓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须有融会贯通脱然无碍。”一旦贯通,也就达到朱熹所说的“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民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平心而论,理学的格物致知具有朴素反映论的色彩。
丹溪抱着“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的目的研究医学,注重通过医学研究推进“心知”,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这既不同于“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纯粹实用性目的;也有异于“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以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的从医动机;更与“沦迹于医”的隐逸风度不相干。因此,丹溪也就更注重从实践,从具体的“物”中去寻求规律,去体味“知”和“道”,具有更严谨的理论态度,研究起点也就更高一些。
具体的“格物致知”例子,如《张子和攻击注论》记载了丹溪随罗太无习医印象最深的二件事:一是从一个病僧的治疗过程中“大悟攻击之法,必其人充实,禀质本壮,乃可行也。否则邪去而正气伤”必致坏病;二是随师年半,见罗太无治病并无一定之方,“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这两个大彻大悟,也就是“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之意,达到“心知”,进而由具体的体验上升为理论,“晓理只在此事如此,便晓理之在此彼事亦如此”,完善了“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治疗思想。
其他如“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如“故人诸病,多生于郁”,如“相火论”等等,都是如此“格物致知”所体味到的“理”。
丹溪所以成为一代大家,在于他有着比一般医家更深刻的理论思维,掌握了更锐利的理论武器,因此也就有他人所不能及的理论成果。
(二)辨疑、发挥的治学方法
人们赞赏《局方发挥》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纠正时弊的信心和勇气,也正视由此带来的医学风气改变的结果,但是,往往忽视了隐伏其后的方法论特点。丹溪著作中以发挥、辨疑为题的还有《伤寒论辨》(又题《伤寒辨疑》,佚)、《外科精要发挥》(佚)等,可以说,辨疑发挥是丹溪医学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是他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特点。如果结合理学家疑经改经思潮,结合宋代学术界的疑古考析传统,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宋代学术界的疑古辨伪之风由来已早,北宋庆历(1041—1048)间,疑经、改经、删经渐成学界时尚。刘敞著《七经小传》,提出对儒家经义的怀疑;欧阳修作《童子问》,疑《易十翼》非孔子言;王安石讥《春秋》是“断烂朝报”,撰《三经义》重新解释《诗》《书》《周礼》;司马光疑《孟子》等。到南宋,郑樵疑《诗序》,朱熹疑《孟子》“井田说”,疑《古文尚书》,疑《诗序》,疑《左传》。疑古,主要是为现实服务,丹溪继承了这一传统,更直接受理学师门的影响。丹溪的三世师祖,“北山四先生”的第二位王柏,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即以敢于质疑问难著称;王柏传金履祥,金履祥传许谦,所以丹溪是王柏的三传弟子。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对汉儒错乱经文深为不满,故作《周易本义》《诗集传》《诗序辩说》,删削《孝经》,给《大学》补写《格物传》。王柏继承并发展了朱熹这一学风,甚至把对古代儒家经传的怀疑推向极端。他认为,“先王之经”本不可疑,只是经过秦始皇焚禁之后,“后世不得见先王之全经”,“经既不全,因不可得而不疑”。进而,他由疑经要求改经,“纠正其谬而刊其赘,订其杂而合其离”,使其“复圣人之旧”。由此,他著《诗疑》《书疑》《中庸论》《大学沿革论》《家语考》等。
丹溪继承了师门传统,他读《局方》,很自然地就产生了“古方新证,安能相值”的疑问;对中医经典《内经》《伤寒论》的研究,也沿用了这一疑经治经的方法。戴良《丹溪翁传》载有一事,“罗成之自金陵来见,自以为精仲景学。翁曰:‘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篇断简之余,然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吾每观之,不能无疑。’因略摘疑义数条以示,罗尚未悟。又遇治一疾,翁以阴虚发热而用益阴补血之剂疗之,不三日而愈。罗乃叹曰:‘以某之所见,未免作伤寒治。今翁治此,犹以芎归之性辛温而非阴虚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误乎?’”联系《金匮钩玄》的“伤寒”门,以为“属内伤者,十居八九”,治法主以补中益气汤出入加减,戴良的说法可信。“略摘疑义数条”,已经使人叹服;汇编成书,即为《伤寒论辨》,自然颇足观赏。虽此书已佚,我们无法了解其详,但从戴氏的记载、《金匮钩玄》的零星内容和师门传统来看,丹溪的《伤寒论》研究应以倡言“错简”为特色。对此,其弟子王履有进一步发挥,《医经溯洄集》颇多独创的见解。可以讲,丹溪开明清《伤寒论》研究“错简”一派之先河。
《格致余论》开篇即言,“《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读”;其朝夕钻研,学习方法是“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而湿热相火等“虽谆谆然见于《素问》而诸老犹未表章”,因此有《格致余论》之作。其中有《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辩》,对《内经》的经文和王冰的句读、注释提出异议和改正意见,并明确地申言:“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内经》发明湿热,此为首出。”“后世不知湿热之治法者,太仆启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疑经、改经的目的所在。《中国医籍考》载有丹溪《素问纠略》一书,未见,不知真伪,但从书名看,似乎也是疑经改经之作。《豆疮陈氏方论》《房中补益论》都有类似的写作目的和方法。
丹溪辨疑发挥之作而最具影响的,当数《局方发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之作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重要标志,并言《局方》“盛行于宋元之间,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这“一变”,就是通过论辩质疑的学术论战,清扫了已成为医学发展障碍的局方之学后,促进了医学领域的百家争鸣,医学理论得到迅猛的发展,整个医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欣欣向荣的局面。推究其因,不能不归功于丹溪这种得自理学师传的治学方法。故《郑堂读书记》说:“从此医家之分别门户以相攻击者,自此书始。盖其儒学本渊源于朱子,故仿朱子《杂学辩》例以著书也。”
(三)气—元论的基本观点
丹溪的医学思想是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上,继承刘、张、李诸家学说,“又复参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而形成的。《通书》《正蒙》分别是周敦颐和张载的著作。
理学十分重视气,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著名观点,《正蒙·太和篇》:“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亦即太虚是气的本然状态,聚而为气,散则为太虚,太虚与气只是聚散关系,故而“太虚不能无气”。气和万物也是聚散关系,气聚为万物,物散则回归于气。这样,张载以气为中心,以聚散为过程,提出太虚、气、万物的变化运动构成宇宙,天人一气,而气为最高范畴。张载的思想实质上《内经》学说的继承和发挥,《内经》的基本论点诸如“太虚寥廓,肇基化元”,如“太虚之中,大气举之”,如“天地合气,万物并至”,“气始而生化,气合而有形”等,都是张载气学学说的思想营养。
丹溪在医学领域里承认并坚持气一元论,既是直接继承于祖国医学的唯物主义传统,也是理学思想的自然发挥。丹溪说:“夫自清浊肇分,天以气运于外而摄水,地以形居中而浮于水者也;是气也即天之谓也,自其无极者观之,故曰大气。”又说:“天地以一元之气化生万物……万物同此一气,人灵于物,形与天地参而为三者,以其得气之正而通也。故气升亦升,气浮亦浮,气降亦降,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籥。他引用了邵康节的话,“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也与周敦颐的“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直接有关,但更反映了祖国医学“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思想传统。《阳有余阴不足论》则以天地为万物父母,“人受天地之气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从天地人统一于气的气一元论来阐述自然界的物质性和人同自然界的统一性。
这一思想运用于医学,即以气的升降运动阐述人体的生理,如《局方发挥》言,“夫周流于人之一身以为生者,气也,阳往则阴来,阴往而阳来,一升一降,无有穷已。”“气为阳,宜降,血为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也以此来阐述治疗的基本原则,如其言“气血虚,皆以味补之,味,阴也,气,阳也,补阴精以求其本也。故补之以味,若甘草、地黄、泽泻、五味子、天门冬之类,皆味之厚也”。
医学家坚持这种气一元论的观点并不鲜见,也不困难,因为有《内经》的完备的气学理论在前,又有气病论治的具体理法方药在后。值得注意的只是,丹溪论气并不引证他的先生许谦和五世师祖朱熹的观点,这有其深意所在:朱熹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先,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即以理为道为本,属第一性;而以气为器为用,属第二性,二者关系,“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气由理所派生,“理生气也”。许谦的思想没有超出朱熹的理气说,也坚持理先气后,理气相依的观点。显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医学理论,也不适应丹溪的思想,所以,他就坚决地抛开师门学说而取法于张、周、邵了。
(四)“参以太极之理”的是非得失
丹溪的主要学术观点“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是在刘、张、李诸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复参以太极之理”“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而形成的。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丹溪进行了一番颇具匠心的改造。笔者非常赞赏丹溪先生这一援儒入医、以儒证医的观点与思想方法。
1.理学的“太极之理” 丹溪所参的“太极之理”来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其原文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交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化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焉,五性感物而善恶分,万事出焉。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
这是周敦颐在《易·系辞》“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基础上,系统完整地阐述宇宙产生发展过程的世界生成模式。太极是万物本原,其性状无形无象,不可言说。
朱熹改造周氏《太极图说》,提出“太极理也”的新命题,并以理为宇宙本体和终极本原,视理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并由此展开理的结构理论,构筑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朱熹说:“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以有无为一”。“太极,理也”,这个“理”就成为天地万物的根本发源,“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无此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赅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理又通过气产生出具体的万事万物,“阴阳是气,五行是质,有这质所以做得物事出来;五行虽是质,它又有五行之气,做这物事方得。”这样,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太极图式,就被朱熹替换成“理—气—万物”的图式了。因此,“理在气上”,成为凌驾一切事物之上,主宰天地万物及其运动的最高范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
理是什么呢?除指阴阳五行变化之理外,朱熹认为最主要的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纲常原则。“理则为仁义礼智”,“盖天下有万世不易之常理……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
这样,朱熹通过《太极图说》论证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理”,亦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就是“太极”,是世界的本原,一切客观事物的主宰。
2.“太极之理”的改造 丹溪“参以太极之理”阐发医理,是进行了一番颇具匠心的改造的。《相火论》以太极之理解释君相二火的生成和性质,“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而火有二……”。如同言气不言理一样,丹溪抛开了“无极”而言“太极”,实质上否认了“无极而太极”“无形而有理”,把朱熹给太极下的定义搁置起来,避而不谈。这样,丹溪就回避了朱熹视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的最中心、最关键的内容,使自己的学说免于唯心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丹溪的高明之处。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丹溪强调的是太极的动静运动状态,进而从中引出阴阳。朱熹说:“动静,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理为之主宰也”。虽强调理的主导作用,却不能否认动静运动正是物质性的气的运动。丹溪突出动静,正是吸取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援儒入医,是为了更好地阐明医理。
周敦颐言太极运动强调其程度:“极”,认为只有达到“极”才出现周期性变化,转化到对立的运动状态去,出现“动—静—动”交替变化的过程。丹溪出于他对人体生理的认识,对《太极图说》进行了第二次改造:“动极而静”“静极复动”被一刀砍掉了。这样,太极运动就成为动静并存又有限度的局面,而不再是一种波浪式交替出现的过程。因为丹溪认为生理状态的动静,尤其是“动”是不能太过的,更不要说“极”了,“动极”是一种严重的病理状态,他说:“人之疾病亦生为动,其动之极也,故病而死矣”。丹溪这一观点,也得益于其师许谦的思想。许谦认为,太极生阴阳,是因为阴阳为太极本身所具有,他说:“太极之中,本有阴阳;其动者为阳,静者为阴。生则俱生,非可以先后言也。”“一元混沌而二气分肇,譬犹一木,折之为二,两半同形,何先后之有?”阴阳是作为太极中的两个对立物而存在的。
再者,丹溪变“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为“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把动静二字分别加于阳、阴之后,对《太极图说》进行了第三次改造:动静不仅仅是太极运动的形式和阴阳二气产生的来源,而且成为阴阳二气运动的特点。由此出发,丹溪得出了火“主乎动”“凡动皆属火”的结论,从而为进一步阐发相火生理病理奠定了理论基础。戴良说,“《内经》之言火,盖与太极动而生阳,五性感动之说有合”,丹溪即以此来阐述他的医学理论。
五行是一种物质形态,是阴阳之气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因此具有更具体确切的性质,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亦即“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丹溪却说“唯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跳出了“各一其性”的圈子,直接援引《内经》君相火而赋以新的含义。丹溪阐发医学观点并不受“太极之理”的束缚,也于此可见。
丹溪本阳气主动之说论火的性质,也借鉴了朱熹的见解。朱熹说:“火质阳而性本阴……外明而内暗,以其根于阴也”,这本是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的对立统一观点的反映。丹溪据以言火的性质,“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姜春华教授对此大为赞赏,“火系物质的燃烧,内中指阴,外燃指阳,极合科学”。这当然是丹溪吸取理学合理内核的成绩。
3.阴阳动静观和生理病理 丹溪“参以太极之理”阐述“火”的生成机理和性质,目的在于提出预防和治疗火病的方法,奠定他的养生论和火热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丹溪引用《易传》“吉凶晦吝生乎动”来说明“动”的二重性,“人有此生,亦恒于动”,过动则“煎熬真阴”而病。由于《相火论》的主旨在发挥相火病因病机,他更强调“动”的病理意义,申明“静”的作用在于维持相火生理状态。这是丹溪动静观的中心问题。
所谓“动”,丹溪特别注重精神情志活动而不及形体体力活动。细究其因,一是丹溪相火属内生火热,病因援用《三因方》“内所因唯属七情交错,爱恶相胜而为病”;一是借用和发挥“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善恶分,万事出矣”的太极之理,认为精神情志活动都属“阳动”之列,“极”则为妄致疾,这又和河间“五志皆能化火”之说相合。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存在:“动静”“性命”“主静”“诚”等概念,本身来自佛家,原来就是用以阐述内心世界的,被周、邵吸收运用并没有改变它的原始含义,丹溪援以入医,就更切合其病因观了。
进而,丹溪又用“五性感物”来解释精神情志活动过极的原因。“仁义礼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本是理学家先验的道德伦理,而后天的“感物”才使人有善恶之分,产生出形形色色的万事来。丹溪所谓“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突出“为物所感”,强调外界刺激,自有区别。朱熹又说,“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以心为精神活动主宰;丹溪因之而言“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因此,丹溪就抓住“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两个主要环节订立养生措施,其要点便是一个“静”字。
丹溪又引用《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熹“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来说明无欲而静,心不迁于外物,不为情感所累,则五志之火动皆“中节”,才能维持正常生理。《周子通书》解释道:“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朱熹则说,“谓之正,则是非端得分明,乃智之实也”。可见无欲而静,澄心定志的关键是中正仁义的道德修养。朱熹又说,“静者,性之所以立也”,“故人虽不能不动,而立人极者必主乎静,唯主乎静则其著乎动无不中节而不失其本然之静矣”,意即为理智之静,道德之静,是立性之本,感情行为中节的前提。丹溪深知其趣,援以证医理。《房中补益论》有言,“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医者立教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动于妄也”。丹溪以为医儒之理一致,主静的实质意义即在理智控制感情,以涵养功夫防止心君情志之火妄动,维持正常生理状态。
朱熹的道心、人心,实即天理、人欲,丹溪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宗旨和谨身节欲的医学观点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观。例如,朱熹的学生曾问及,“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熹答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丹溪把这一观点引入《茹淡论》,认为饮食之物“天之所赋者,若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人之所为者,皆烹饪调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因而,“安于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为安者,欲之纵,火之胜也”。丹溪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宋濂称赞他“居室垣墉,敦尚俭仆;服御唯大布宽衣,仅取蔽体;藜羹糗饭,安之如八珍……其清修苦节,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而于世上所悦者,淡然无所嗜”,表彰他以纲常治化要求自己;丹溪自己也说,“年迈七十矣,却尽盐醯”,反而“神茂而色泽”,即是以医儒一致之理自我要求,达到养生目的。
4.“听命于道心”的唯心主义倾向 丹溪以“人心听命于道心而又主之以静”,作为相火“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表现出明显的唯心倾向,既削弱了相火生理说的意义,又限制了他对相火病因的进一步认识。这是理学唯心论的消极影响和丹溪作为理学家的思想缺陷。
理学家倡言的“中正仁义”“道心”之类,原意不过要求人们用封建道德观念约束自己,维护封建秩序。丹溪借以说明理智控制感情,防止七情为病,也不失为别出心裁的创见。然而,精神情志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生理活动,若过分强调,甚至作为维持正常生理状态的先决条件,就必然陷于唯心主义。我们只要设想,若是不“听命于道心”,又不“主之以静”的“凡夫俗子”“碌碌众生”有无正常的相火,就足以使丹溪无言以对:承认有,则与自己设想的“道心”“主静”之类的前提矛盾;否认,也就否定了相火生理,同时也不符合事实。丹溪原意可能是通过设立这么个前提,为阐发相火病因留下伏笔,不料竟陷于如此进退两难的矛盾处境,可见这一有唯心倾向的理论实难站得住脚。
在这一错误观点的支配下,丹溪片面强调精神因素的病因意义,生生不息的相火生理失去“道心”节制这一先决条件,直接后果自然就是相火妄动的病理状态了。但是,五志之动触发暴悍酷烈的相火妄动证,只有可能而没有其必然性。丹溪之误固然与他囿于《三因方》有关,也不能不归咎“道心”“主静”之类。所以,相火病因和这个先决条件,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它限制了丹溪对相火病因的进一步探索,而仅仅停留在精神情志这一狭窄的范围里。事实上,丹溪已发现许多因素可以导致相火妄动,“大劳则火起于筋,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谷与肥鲜同进,厚味得谷为助,其积之久也,宁不助阴火而致毒乎?”可惜都不曾提高到理论高度去认识。这又是这种唯心主义倾向给丹溪带来局限。
5.“参以太极之理”和命门学说 丹溪援儒入医,“参以太极之理”阐述医学问题,是一大发明,明代赵献可、孙一奎、张景岳等人继承了这种思维和论证方法,建立命门学说。姜春华教授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他说,“丹溪首先引用周子《太极图说》之‘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说以论相火”,“赵、张、孙三氏均以宋儒太极之说以解释人体生命之奥秘”,“医家以为命门与太极有相似之义,遂成为中医学上之重要学说”。
同样是“参以太极之理”,赵、张、孙运用得比丹溪更妥帖,论证更完善,也更彻底地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因素。首先,他们一致强调太极的存在,从中直接引出命门的概念,这比丹溪回避太极含义,只重动静运动,更具体切实,也更明确地表达了气一元论的唯物立场。其次,他们强调太极所生的阴阳——命门真水真火的生理意义,借“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来说明“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由此把命门相火真水同全身的脏腑气血阴阳紧密联系起来。这比空泛地议论“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当然丰富多彩。从这种生理意义出发,很自然引出命门阴阳水火不足的病理状态,由此提出一系列独具只眼的见解和匠心独运的方剂,把理论和临床贯穿起来,这方面丹溪考虑得远不如他们周到。再次,命门学说认为命门水火阴阳的发生和存在,纯粹是一种生理现象,“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的发展起来的,根本不存在什么“道心”之类的前提条件,避免了丹溪唯心主义倾向。孙一奎引朱熹“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统体一太极,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的“理一分殊”说,论证“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中一物尔,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证明命门即自然存在的人体太极。
小结
丹溪援儒入医,是思想方法的进步,其医学理论有了坚定的思想基础。影响所及,使祖国医学理论在明清一代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形成了哲学思想进入医学领域的第二次高潮,其中有丹溪所起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刘时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