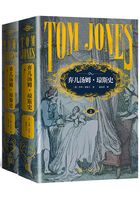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八章
诗神用荷马的风格,唱出来的一场战斗,除了古典文学读者,无人能知其味。
威斯屯先生在这个教区上,也有一份产业,这个教区的教堂,比他自己的教区上的那个,离他的家远不了多少,所以他也常常到这个教堂来做礼拜;这一次,他和可爱的苏菲娅,碰巧都在场。
苏菲娅很喜欢媢丽长得好看。她看到媢丽那样一打扮,因而惹得和她同类的人都嫉妒起来,只可怜她头脑简单。她刚一回到家里,就把猎守叫来,吩咐他,叫他把他女儿带到她跟前。她说,她要媢丽到她家来,她供媢丽食住,同时,她现在这个女仆正打算要走,如果这个女仆当真走了,她也许还要把媢丽放在自己身边。
可怜的西格锐姆一听这话,如同听到一声霹雳;因为他对他女儿身体方面异于旧日的情况,并不生疏。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恐怕媢丽这孩子,太笨手笨脚了,不会伺候小姐您,因为她从来没出来伺候过人。”“那不要紧,”苏菲娅说,“她跟着我,不久就可以学得心灵手巧了。我很喜欢这孩子,一定要叫她来试试看。”
黑乔治现在去找他太太,打算听一听她有什么好主意,能使他从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里解脱出来。但是他到了家里一看,家里正一团糟。原来那件肥大的长袍,惹起了那么大的嫉妒,所以当奥维资先生和别的绅士离开教堂以后,人们在这以前憋而未发的怨气一下爆炸,变成一片狂叫乱喊;起先大家只七嘴八舌、冷讽热嘲、大呼小叫、手指脚画、叱责怒骂;最后竟动起可供抛掷投扔的武器来。这种武器,虽然由于本身刚柔随意,不至于伤害性命,戕贼肢体,但是对于衣着华丽的女人,却很足以引起惶恐。媢丽本是一个性刚胆烈的女孩子,不能老老实实地忍受这一套,因此——不过且住,既是我们不敢自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场战斗描绘出来,那让我们请一位才大艺高的能手,助我们一臂之力好啦。
哦,汝缪斯之属呵,不问是谁,凡喜歌咏战争者,特别是您,前此曾叙休狄布莱斯与徂拉交战战场上之屠杀者,如汝尚未与汝之友人勃特勒一同饿死,即请汝在此一次重要场合中,助我描绘战迹可也![勃特勒在《休狄布莱斯》第1部第2章中,言休狄布莱斯,遇一群看逗牛的人,与之交战[休狄布莱斯为清教徒,反对逗牛(bull-baiting,非斗牛,bull-fight)之戏],其对手之一为徂拉。第365—408行,言徂拉为一胆大泼妇,壮实而高大,等等。勃特勒据传说,老年受人冷落,饥饿而死。故这儿有“如果勃特勒还未饿死”之语。他晚年穷困,但饿死是说者过甚其词。勃特勒在这段诗之前,亦曾呼缪斯助之,故言助勃特勒写此一段之缪斯。此已见前注。](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469CF6/14711229805667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6553196-u7NemthdpcJ2OspwPCq5MbFCYv6W5bFc-0-315344bab7bc4750264786e6a85c476b) 。并非所有之人均能做所有之事。
。并非所有之人均能做所有之事。
一个家道兴旺的农人,在他的场院里,如果有一大群母牛,在挤奶的时候,听到远处的牛犊,因为正在进行中的掠夺行为而发出哀号之声,那些母牛就要又大肆怒吼,大发长哞;当时萨姆塞特郡的群氓,就像那种母牛那样,高喊狂叫,一片怒吼,在这一片怒吼之中,有各式各样的尖叫、嘶喊,以及其他不同的诟詈、辱骂;总之,有多少不同的人,或者实在说,有多少不同的感情,就有多少不同的声音:其中有的人,就由于愤怒而大叫,又有的人,就由于恐惧而惊呼,另有一些人,脑子里并没有任何念头,只是觉得一齐起哄很好玩,也跟着喧嚷起来,但是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嫉妒;她是撒旦的亲姊妹,永远跟随在他的身边;她在人群中冲来冲去,煽惑妇女,叫她们发威动怒。她们刚追上了媢丽,就纷纷抓起脏土和垃圾来,朝着她扔去。
媢丽本来尽力想要全师振旅,从容撤退,但是并没能够如愿以偿,所以现在回头转身,面临大敌。她先抓住了衣服褴褛的白斯(她是敌人中站在最前列的),把她一下打得趴在地上。于是敌人的全部人马(虽然数起来有一百之多),看到她们的主帅遭到的命运,往后倒退了好些步,躲到一个新掘的坟圹后面;因为她们的战场,就是教堂的坟地;就是那天晚上,要有一家,在那儿举行殡仪注6。媢丽乘胜追击,从坟圹边儿上抓起一个放在那儿的髑髅来 ,往前投去,那样凶猛,一下打到一个成衣匠的脑壳上。这两颗脑壳,同样发出一种空穴来风的声音,成衣匠一下来了个嘴啃泥,倒卧地上,把地皮占了一大块。于是两颗脑壳,平列地上,而这两颗,究竟哪一颗更有价值,是很令人拿不定的。媢丽于是又抓起一条大腿骨来
,往前投去,那样凶猛,一下打到一个成衣匠的脑壳上。这两颗脑壳,同样发出一种空穴来风的声音,成衣匠一下来了个嘴啃泥,倒卧地上,把地皮占了一大块。于是两颗脑壳,平列地上,而这两颗,究竟哪一颗更有价值,是很令人拿不定的。媢丽于是又抓起一条大腿骨来 ,冲到那群逃跑的人中间,把大腿骨一左一右,大肆挥舞,把好多伟大的英雄和英雌,都打得伟躯栽倒,玉体倾跌。
,冲到那群逃跑的人中间,把大腿骨一左一右,大肆挥舞,把好多伟大的英雄和英雌,都打得伟躯栽倒,玉体倾跌。
注6英国18世纪,葬仪特讲排场铺张,每一个小商人,死时亦须有“灵 ”及半打送丧车随其后,虽教堂坟地不过一百码之遥。且葬仪多于夜间行之,以便雇来的“小喃儿”,手执蜡心火把,通明照眼,更显殡仪气派。见毕赞特《伦敦》第9章。但在布阑得的《大不列颠民间古风旧俗之观察》第2卷第276页《葬仪中之火把》条下注2说,“在罗马人中,公葬在日间举行,私葬在夜间举行。二者都伴之以火把。”又说,“古代一切葬仪,均于夜间行之,伴以火把。为的是白昼举行,怕于路上为僧侣及治安法官所见,因他们如见死尸,则他们神圣之质受到侵犯,总得举行赎罪献牲之仪式,始能再执行职务。”
”及半打送丧车随其后,虽教堂坟地不过一百码之遥。且葬仪多于夜间行之,以便雇来的“小喃儿”,手执蜡心火把,通明照眼,更显殡仪气派。见毕赞特《伦敦》第9章。但在布阑得的《大不列颠民间古风旧俗之观察》第2卷第276页《葬仪中之火把》条下注2说,“在罗马人中,公葬在日间举行,私葬在夜间举行。二者都伴之以火把。”又说,“古代一切葬仪,均于夜间行之,伴以火把。为的是白昼举行,怕于路上为僧侣及治安法官所见,因他们如见死尸,则他们神圣之质受到侵犯,总得举行赎罪献牲之仪式,始能再执行职务。”
哦,缪斯呵,请您把那一天舍生冒死的、倒地的都姓甚名谁,表明一番。首先,捷米·特维得勒,在脑勺子上,叫这块可怕的大腿骨,击中了一下。他是那条秀丽蜿蜒的司陶厄河 林野幽美的两岸,把他哺乳大的,就在那儿,他第一次学会了以音表情的艺术;他就身挟此技,往来于地方圣节
林野幽美的两岸,把他哺乳大的,就在那儿,他第一次学会了以音表情的艺术;他就身挟此技,往来于地方圣节 和庙会,给乡间的林仙与狡童,在青草地上穿插交互翩翩起舞的时候,从旁鼓励助兴;他自己呢,就站在那儿演奏提琴,随着自己奏的乐声而欢跳。现在他的提琴,于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他的躯体,现在把青草地都砸了一个坑。第二个是老伊齐浦勒,一个骟猪的,他在前额上让我们这位爱末怎式的女英雄,打中了一下,马上就身倒地上。他是一个走起来摇摇摆摆的胖家伙,他这一倒下,其声音之大,就像塌了一所房子一样。他的烟盒,从他的口袋儿里,同时掉了出来,媢丽就把它作为合法的掠获物,劫夺而去。磨坊的凯特,不幸叫墓碑绊了一跤,她那没系袜带的袜子,就挂在墓碑上,于是她来了一个冠履倒置,脚上头下。白提·批品,连带她那位年轻的情人,两个双双跌倒地上,在那儿,哦,行事倒颠的命运呵,她匍匐在地,而他却仰面朝天。托姆·夫莱克勒,一个铁匠的儿子,是媢丽的怒气下另一个受灾难的人。他是一个手儿很巧的匠人,做得一手好木头套鞋
和庙会,给乡间的林仙与狡童,在青草地上穿插交互翩翩起舞的时候,从旁鼓励助兴;他自己呢,就站在那儿演奏提琴,随着自己奏的乐声而欢跳。现在他的提琴,于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他的躯体,现在把青草地都砸了一个坑。第二个是老伊齐浦勒,一个骟猪的,他在前额上让我们这位爱末怎式的女英雄,打中了一下,马上就身倒地上。他是一个走起来摇摇摆摆的胖家伙,他这一倒下,其声音之大,就像塌了一所房子一样。他的烟盒,从他的口袋儿里,同时掉了出来,媢丽就把它作为合法的掠获物,劫夺而去。磨坊的凯特,不幸叫墓碑绊了一跤,她那没系袜带的袜子,就挂在墓碑上,于是她来了一个冠履倒置,脚上头下。白提·批品,连带她那位年轻的情人,两个双双跌倒地上,在那儿,哦,行事倒颠的命运呵,她匍匐在地,而他却仰面朝天。托姆·夫莱克勒,一个铁匠的儿子,是媢丽的怒气下另一个受灾难的人。他是一个手儿很巧的匠人,做得一手好木头套鞋 活计;不但这样,把他打倒了的那只木头套鞋,就正是他自己一手的出品。如果他那时候在教堂里唱圣诗,那他就可以免于脑袋“开瓢”了。克娄姑娘,一个农民的女儿;约翰·忌狄什,他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南·斯劳齐、艾斯特·考得令、维勒·斯浦锐、托姆·奔奈特、杷特三姊妹(她们的爸爸是开客店的,招牌上有红狮为记)、内室女侍白提、马夫捷克,还有一些等而下之的人物,都躺在坟墓中间打滚。
活计;不但这样,把他打倒了的那只木头套鞋,就正是他自己一手的出品。如果他那时候在教堂里唱圣诗,那他就可以免于脑袋“开瓢”了。克娄姑娘,一个农民的女儿;约翰·忌狄什,他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南·斯劳齐、艾斯特·考得令、维勒·斯浦锐、托姆·奔奈特、杷特三姊妹(她们的爸爸是开客店的,招牌上有红狮为记)、内室女侍白提、马夫捷克,还有一些等而下之的人物,都躺在坟墓中间打滚。
所有这些,并不都是媢丽的胳膊有劲的关系,因为有好多人,争着逃跑的时候,互相撞倒了。
但是命运现在,害怕自己的行动已经有失本色,再加上她偏向一边,特别是对的那一边,时间太久了,所以急忙来了一个大转弯;因为现在布朗大娘挺身而出——她是她丈夫搂抱怀中的宝贝儿,不但她丈夫自己,还有全区上一半的人,都在怀里搂抱过她;她在维纳斯 的战场上,就这样出名,但她实在在玛斯
的战场上,就这样出名,但她实在在玛斯 的战场上,也不弱于在维纳斯的战场上。这两种胜利的纪念品,她丈夫永远戴在头上和脸上;如果从来有人,曾以头上之角
的战场上,也不弱于在维纳斯的战场上。这两种胜利的纪念品,她丈夫永远戴在头上和脸上;如果从来有人,曾以头上之角 显耀他太太在兼收并蓄一方面的光荣的,以西结就那么干过。他脸上纵横阑干的伤痕,同样表示,她不但有善做手脚的才能,还有善使手脚的本事。
显耀他太太在兼收并蓄一方面的光荣的,以西结就那么干过。他脸上纵横阑干的伤痕,同样表示,她不但有善做手脚的才能,还有善使手脚的本事。
这个爱末怎,现在对于她那一党可耻的逃跑,再也忍不下去了。她一下站住,高声对那些逃跑的人说道:“你们这些萨姆塞特郡的人啊,再不就该说,你们这些萨姆塞特郡的女人啊,你们叫这样一个单人匹马的臭丫头片子,打得七零八落,东跑西颠,你们不害臊吗?不过要是没有别人敢和她交手,可别说我自己和昭安·塔浦要抢胜利的功劳。”她这样说完了,就扑向媢丽·西格锐姆,很容易就把那块大腿骨,从她手里抢了过来,同时还把她的便帽,从她头上给她抓了下来。于是她用左手抓住了媢丽的头发,用右手使劲打媢丽的脸,一会儿的工夫,鲜血就从媢丽的鼻子里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媢丽在这个时间里也并没闲着。她一下就把布朗大娘的包头布,从她头上揪了下来,用一只手紧紧抓住了她的头发,用另一只手把她的敌人打得鲜血也从鼻孔里往外如泉之涌。
这两个女战士,每一个从敌人头上掠夺了足够的俘获物——头发——以后,她们又把她们的怒气冲着衣服发作起来。在这番干仗中,她们双方都勇猛异常,所以一会儿的工夫,她们两个都是从腰部以上,全都赤裸。
妇女用拳头交起手来的时候,她们攻击的部位和男人不同, 这是她们侥幸的地方。但是,虽然她们也会稍违本性,出阵决战,而据我所看见过的,她们却从来没有完全忘记本性,而互相在乳部攻打。因为在那儿只打几下,就可以把她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完全交代了。这种不打乳部的情况,我知道,有些人认为,只是由于她们嗜血成性,远过于男性。正因为如此,她们才老找鼻子的碴儿,因为那个地方最容易使鲜血喷出。不过这种假设,有些牵强附会,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这是她们侥幸的地方。但是,虽然她们也会稍违本性,出阵决战,而据我所看见过的,她们却从来没有完全忘记本性,而互相在乳部攻打。因为在那儿只打几下,就可以把她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完全交代了。这种不打乳部的情况,我知道,有些人认为,只是由于她们嗜血成性,远过于男性。正因为如此,她们才老找鼻子的碴儿,因为那个地方最容易使鲜血喷出。不过这种假设,有些牵强附会,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在这一点上,布朗大娘却大大地占了媢丽的便宜;因为布朗大娘实在并无乳部可言;她的乳部(我们姑且这样叫吧)不论在颜色方面,也不论在许多别的性质方面,都完全像一块古代的羊皮纸一样,在它上面,不论谁,都可以捶打很大的工夫,而对它没有任何的伤损。
媢丽除了她现在这种不幸的情况而外,在那一部分还异常发达,很有可能使布朗大娘看着生妒,因而给她一下致命伤;如果不是侥幸,汤姆恰好在这个时候来到跟前,使这一场血战马上中止。
他这样偶然来到,得侥幸归功于斯侩厄先生;因为,他、卜利福少爷和琼斯,做完了礼拜以后,骑在马上闲溜达,往前走了有一英里的四分之一;那时候,斯侩厄改变了主意(并不是随便就改变了的,而是别有用心,这我们有工夫的时候,再对读者表明),要叫那两位年轻的绅士,不要照原来的打算,而另取路而行。他这个提议;那两位年轻绅士赞同,于是他们就必然又回到了教堂坟地。
卜利福少爷骑着马走在前面,看到了聚了一群人,又看到那两个女战士在那儿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正杀得难分难解;他把马停住,打听是怎么回事。一个乡下人,一面挠脑袋,一面回答他说:“我可说不好,少爷,我可说不好;不过您要是想要知道知道,这不是布朗大娘和媢丽·西格锐姆两个干起来了吗?”
“谁?谁?”汤姆喊道;但是没等听到回答,就看到他那位媢丽,在这场武戏里,脸上弄出来的光景;所以他急忙下了马,也不顾得拴马,就跳过坟地的短墙,跑到媢丽跟前。她一见他,才头一次哭起来,告诉他,他们都怎么对她行凶动蛮。他一听这话,竟忘了布朗大娘的性别,或者也许在他的愤怒中,不知道她是什么性别——因为,说实在的,她除了穿着一条衬裙,别的方面,就都看不出来她是女性,而那条衬裙,汤姆也许没看见——拿起马鞭子来,就抽了她几下;跟着他又飞奔到人群中(因为媢丽把他们一齐都告下来了),前后左右,一概鞭如雨下,乱抽乱挥起来。如果我不把诗神再召唤出来,那我就不能重叙那天那种马鞭狂挥的光景。不过好心眼儿的读者,也许要认为,诗神那天已经累得汗水淋漓了,不要苦苦地再逼她了。
他像荷马的英雄真正做过的那样,或者像堂吉诃德或者任何到处行侠仗义的游侠骑士所能做的那样,奋勇扬威,把敌人的整个战线都横扫了一遍,才回到媢丽身边。只见媢丽那时那种光景,要是我非在这儿绘声绘影都描写出来不可,那就一定不但要使我自己,而且还要使读者,同样心如刀割。汤姆像个疯子一样,咆哮叫骂,捶胸薅发,顿足震地,起誓呼天,要对所有一切参与其事的人,都极尽报仇雪恨之能事。于是他把自己的褂子,从身上剥下来,围在媢丽身上,把纽扣给她系好;把自己的帽子,戴在她头上;用手绢尽其所能,把她脸上的血给她擦掉;大声吩咐仆人,叫他尽力快快骑马,取一个偏鞍或后鞍来,以便把她平平安安地送回家去。
卜利福少爷本来反对打发仆人回去,因为他们只有一个仆人跟随。但是既然斯侩厄对汤姆的吩咐加以附议,他无可奈何,也只好听命了。
仆人一会儿就带着一副后鞍回来了;这时媢丽把她那身撕破了的衣服,尽其所能,在身上往一块凑拢了之后,弄到马上仆人的身后。就这样,她骑着马回到家里,斯侩厄、卜利福少爷和琼斯做了护送。
在那儿,汤姆接回他自己的褂子,趁人不见,偷偷吻了她一下,悄悄地告诉她,说晚上再来看她,然后才离开了他那位媢丽,骑上马追他的同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