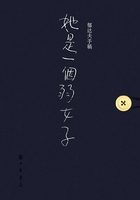
序言
保存、整理和研究作家的创作手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笔者十多年前就提出要“重视手稿学的研究” ,后来又有论者进一步重申和发挥,研究现代作家手稿的学术成果也已陆续出现。
,后来又有论者进一步重申和发挥,研究现代作家手稿的学术成果也已陆续出现。 但是,与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重要作家手稿不断印行
但是,与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重要作家手稿不断印行 相比,郁达夫这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灭印记的创造社代表作家的手稿的出版和研究,实在是乏善可陈,连他的中学同学、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存世手稿也早已问世
相比,郁达夫这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灭印记的创造社代表作家的手稿的出版和研究,实在是乏善可陈,连他的中学同学、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存世手稿也早已问世 ,但他除了致王映霞书信部分手稿已经印行外
,但他除了致王映霞书信部分手稿已经印行外 ,还可以说些什么呢?
,还可以说些什么呢?
不妨先回顾郁达夫手稿的发表情况。
在郁达夫生前,他的新文学创作手稿的刊登仅见二次。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达夫自选集》时,书前刊出了《序》手稿之一页;1935年3月,郁达夫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出版时,《良友图画杂志》《新小说》等刊出了他的《编选感想》手稿一页。在郁达夫身后,他的一些旧体诗词手稿在海内外陆续有所披露,但小说、散文、杂文、评论等新文学作品手稿的发表,哪怕只有一页也好,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也几乎完全空白。
1982年至1985年,广州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郁达夫文集》(12卷本),作为插图之用的郁达夫新文学作品手稿共刊出如下数种:
中篇小说《迷羊》第二章第一页;
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第一章第一页;
《〈达夫自选集〉序》之一页;
随感《〈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编选感想》;
评论《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第一页;
《厌炎日记》第一页;
译文《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高尔基作)之一页。
1992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全集》(12卷本),新刊出的作为插图之用的郁达夫创作手稿仅有如下二种:
短篇小说《圆明园的秋夜》第一页;
1929年9月27日(旧历八月廿五)日记之一页。
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的《郁达夫全集》,刊出的插图中,除了一些诗词和题词等手迹,郁达夫新文学作品手稿的蒐集并无进展。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已披露的郁达夫新文学作品手稿中,仅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编选感想》一页是一篇完整的手稿,其它都只是文中一个小小的片段而已。换言之,除了这篇短小的《编选感想》,迄今为止,郁达夫完整的新文学作品手稿从未与世人见面。由此足见,郁达夫手稿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严重滞后。由此也有力地证明,郁达夫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的影印问世,不仅使读者能够欣赏难得一见的郁达夫钢笔书法,对郁达夫手稿的研究更是零的突破,对整个郁达夫研究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郁达夫小说创作史上,《她是一个弱女子》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这是郁达夫继《沉沦》《迷羊》之后出版的第三部中篇。小说以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后至“一·二八事变”为背景,以女学生郑秀岳的成长经历和情感纠葛为主线,描绘了她和冯世芬、李文卿三个青年女性的不同人生道路和她的悲惨结局。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过程,正如郁达夫自己在《〈她是一个弱女子〉后叙》中所说:
《她是一个弱女子》的题材,我在一九二七年(见《日记九种》第五十一页一月十日的日记)就想好了,可是以后辗转流离,终于没有功夫把它写出。这一回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来侵,我于逃难之余,倒得了十日的空闲,所以就在这十日内,猫猫虎虎地试写了一个大概。
查《日记九种·村居日记》,在1927年1月10日日记中,郁达夫先记下了他完成周作人大为赏识的短篇《过去》,并打算一鼓作气续完中篇《迷羊》的感受,强调自己的“创作力还并不衰”,然后写道:
未成的小说,在这几月内要做成的,有三篇:一,《蜃楼》;二,《她是一个弱女子》;三,《春潮》。此外还有广东的一年生活,也尽够十万字写,题名可作《清明前后》,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也必须于今年写成才好。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计划,如能全部实现,那该多好。可惜后来中篇《蜃楼》只发表了前12章 ,《春潮》无以为继
,《春潮》无以为继 ,《清明前后》毫无踪影,“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也只是一个设想,唯独《她是一个弱女子》虽然拖延了不少时日,终于按计划大功告成。
,《清明前后》毫无踪影,“明清之际的一篇历史小说”也只是一个设想,唯独《她是一个弱女子》虽然拖延了不少时日,终于按计划大功告成。
从《她是一个弱女子》作者题记和末尾《后叙》的落款时间可知,这部作品1932年3月杀青,正值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之际,郁达夫后来在《沪战中的生活》中对写作《她是一个弱女子》的经过又有进一步的回忆:
……在战期里为经济所逼,用了最大的速力写出来的一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这小说的题材,我是在好几年前就想好了的,不过有许多细节和近事,是在这一次的沪战中,因为阅旧时的日记,才编好穿插进去,用作点缀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哪一条路。三个女性中间,不消说一个是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堕落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犹豫不决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这小说的情节人物,当然是凭空的捏造,实际上既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也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的。
必须指出,郁达夫这段话已把他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塑造三个不同的年轻女性的创作宗旨和盘托出,小说中这三位女子的同性恋纠葛也应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才有意义。但是,后来竟有人自动对号入座,认为这部小说是在影射作者自己的家庭纠纷 ,未免把小说创作和现实生活混为一谈。
,未免把小说创作和现实生活混为一谈。
《她是一个弱女子》完稿后,并没有像《蜃楼》那样先在刊物上连载,而是像《沉沦》《迷羊》那样直接交付出版。1932年3月31日,此书由上海湖风书局付梓,4月20日出版,列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印数1500册。据唐弢查考,《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后不久即被当局指为“普罗文艺”而禁止发行。湖风书局被查封后,上海现代书局接收湖风书局纸型于当年12月重印,但为了躲过检查,倒填年月作“1928年12月”初版,又被当局加上“妨碍善良风俗”的罪名,下令删改后方可发行。次年12月,删改本易名《饶了她》重排出版,不到半年又被当局认定“诋毁政府”而查禁。 《她是一个弱女子》命途如此多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它这样一再被查禁的作品,并不多见。
《她是一个弱女子》命途如此多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它这样一再被查禁的作品,并不多见。
对郁达夫这部中篇的评价长期以来也是毁誉参半。湖风初版本问世不到四个月,就有论者撰文评论,认为“这依然是一部写色情的作品”,“在结构和文章上都并不十分出色,可是它的描划人物都是非常成功的。作者本是这方面的能手。他写郑秀岳的弱,写李文卿的不堪,都能给予读者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形象。这是不依靠文字的堆琢的白描的手段,在国内作品中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也有论者认为《她是一个弱女子》“不失为郁先生作品中的杰作之一”
也有论者认为《她是一个弱女子》“不失为郁先生作品中的杰作之一” 。1950年代初,论者在批评《她是一个弱女子》“对革命人物的塑造”“显得有些浮沉平面”,反让“他过去作品中的主调——肉欲和色情的描写占了上风”的同时,还承认“这篇小说在达夫先生作品中仍不失为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
。1950年代初,论者在批评《她是一个弱女子》“对革命人物的塑造”“显得有些浮沉平面”,反让“他过去作品中的主调——肉欲和色情的描写占了上风”的同时,还承认“这篇小说在达夫先生作品中仍不失为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 但随着认为郁达夫作品有很大消极面的看法占据统治地位,《达夫全集》胎死腹中
但随着认为郁达夫作品有很大消极面的看法占据统治地位,《达夫全集》胎死腹中 ,《她是一个弱女子》这样的作品当然也无法重印,更难以展开探讨了。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她是一个弱女子》才在问世半个世纪后首次编入《郁达夫文集》重印,这部中篇手稿的第一页也作为插图首次与读者见面。但是,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对《她是一个弱女子》仍然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评价不高。
,《她是一个弱女子》这样的作品当然也无法重印,更难以展开探讨了。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她是一个弱女子》才在问世半个世纪后首次编入《郁达夫文集》重印,这部中篇手稿的第一页也作为插图首次与读者见面。但是,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对《她是一个弱女子》仍然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评价不高。 近年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已有研究者重新注意《她是一个弱女子》,重新研究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试图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女同性恋理论、心理分析理论等重新解读这部中篇小说。
近年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已有研究者重新注意《她是一个弱女子》,重新研究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试图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女同性恋理论、心理分析理论等重新解读这部中篇小说。
《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书于名为“东京创作用纸”的200格(10×20)稿纸之上,黑墨水书写,共154页(绝大部分一页二面,也有个别一页一面),又有题词页1页,对折装订成册,封面有郁达夫亲书书名:“她是一个弱女子”。除了封面略为受损和沾上一些油渍以及第21页左面撕去一部分外,整部手稿有头有尾,保存完好,只是书末缺少了达夫作于1932年3月的此书《后叙》,想必《后叙》是他在此书交稿后或校阅清样时所作,未包括在这册手稿本中。
翻阅这部《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打开第一页就有个不小的发现。《她是一个弱女子》初版本题词上印有: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最尊敬的映霞。一九三二年三月达夫上
但是手稿题词页明明写着: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最尊敬的映霞。五年间的热爱,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你那颗纯洁的心。一九三二年三月达夫上
不过,后一句又被作者全部划掉了。由此可知,这段题词原来有两句,但最后付梓时,郁达夫删去了后一句,仅保留了第一句。为什么要删去?耐人寻味。
经与《她是一个弱女子》初版本核对,又可知这部手稿既是初稿,又是在初稿基础上大加修改的改定稿,颇具研究价值。手稿本从头至尾,几乎每一页都有修改,大部分用黑笔,偶尔用红笔的修改,或涂改,或删弃,或增补,包括大段的增补。有时一页修改有九、十处之多,还有一些页有不止一次修改的笔迹。郁达夫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认真细致、反复斟酌,由此可见一斑。
品读手稿,我们可以揣摩郁达夫怎样谋篇布局,怎样遣词造句,怎样交代时代背景,怎样描写风土人情,怎样设计人物对话,怎样塑造主人公形象,一言以蔽之,可以窥见郁达夫是怎么修改小说的。这样的例子在手稿本中俯拾皆是,不妨举几例。
在交代时代背景方面,小说第二章写主人公郑秀岳求学经历,手稿初稿有这么一小段:
政潮起伏,时间一年年的过去,郑秀岳居然长成得秀媚可人,已经在杭州的女学校里,考列在一级之首了。
手稿上修改后的定稿,也即初版本所印出的这一段是这样的:
政潮起伏,军阀横行,中国在内乱外患不断之中,时间一年年的过去,郑秀岳居然长成得秀媚可人,已经在杭州的这有名的女学校里,考列在一级之首了。
两相比较,手稿上增添的这些字句显然并非可有可无。
再如小说第十六章中,写到国共合作北伐时,手稿初稿有这么一段:
孙传芳占据东南不上数月,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军队,受了第三国际的领导和工农大众的扶持,着着进逼。革命军到处,百姓箪食壶浆,欢迎唯恐不及。于是军阀的残部,就不得不露出他们的最后毒牙,来向无辜的百姓,试一次致命的噬咬。可怜杭州的许多女校,同时都受到了匪军的包围,几千女生同时都成了被征服地的人身供物。
而手稿上修改后的定稿,也即初版本所印出的这一段是这样的:
孙传芳占据东南五省不上几月,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军队,受了第三国际的领导和工农大众的扶持,着着进逼,已攻下了武汉,攻下了福建,迫近江浙的境界来了。革命军到处,百姓箪食壶浆,欢迎唯恐不及。于是旧军阀的残部,在放弃地盘之先,就不得不露出他们的最后毒牙,来向无辜的农工百姓,试一次致命的噬咬,来一次绝命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可怜杭州的许多女校,这时候同时都受了这些孙传芳部下匪军的包围,几千女生也同时都成了被征服地的人身供物。
两相比较,手稿定稿修改增添的字句,当然更具体,更准确,作者的态度也更爱憎分明,更能激起读者的愤怒和同情。
在描写景物和人物心情方面,小说第二十一章写到郑秀岳和吴一粟坠入爱河,手稿初稿有这么一段:
这时候黄黄的海水,在太阳光底下吐气发光,一只进口的轮船,远远地从烟突里放出了一大卷烟。从小就住在杭州,并未接触过海天空阔的大景过的郑秀岳,坐在海风飘拂的回廊阴处,吃吃看看,和吴一粟笑笑谈谈,觉得她周围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她和吴一粟两个人,只有她和他,像是亚当夏娃一样,在绿树深沉的伊甸园里过着无邪的日子。
手稿修改后的定稿,也即初版本所印出的则作:
这时候黄黄的海水,在太阳光底下吐气发光,一只进口的轮船,远远地从烟突里放出了一大卷烟雾。对面远处,是崇明的一缕长堤,看起来仿佛是梦里的烟景。从小就住在杭州,并未接触过海天空阔的大景过的郑秀岳,坐在海风飘拂的这旅馆的回廊阴处,吃吃看看,更和吴一粟笑笑谈谈,就觉得她周围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她和吴一粟两人,只有她和他,像是亚当夏娃一样,现在坐在绿树深沉的伊甸园里过着无邪的原始的日子。
显而易见,经过修改补充的手稿定稿更细腻,更生动,更好地烘托出主人公两情相悦的欢快心情。
《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所展示的作者的各种修改,当然举不胜举,读者如果仔细比对,一定还会有许许多多有趣的发现。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中,有“文本发生学”一脉,也即“考察一个文本从手稿到成书的演化过程,从而探寻种种事实证据,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审核形式、创作中的合作与修订等问题”。 就发生学研究而言,手稿(包括草稿、初稿、修改稿、定稿乃至出版后的再修订稿等)的存在和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大大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捕捉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文本。以此观之,《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的影印出版,就意义决非一般了,因为它为我们进一步打开探讨这部备受争议的郁达夫小说的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
就发生学研究而言,手稿(包括草稿、初稿、修改稿、定稿乃至出版后的再修订稿等)的存在和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大大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捕捉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文本。以此观之,《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的影印出版,就意义决非一般了,因为它为我们进一步打开探讨这部备受争议的郁达夫小说的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
总之,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雨沧桑,《她是一个弱女子》完整的、同时也是十分珍贵的手稿得以幸存于世,毫不夸张地说,确实是郁达夫研究的大幸,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作家手稿研究的大幸。这部手稿得以完好地保存,郁氏后人功不可没。当年手稿正文第一页首先在《郁达夫文集》刊出,就是原收藏者、郁达夫长子郁天民先生热情提供的。关于这部手稿本的收藏经过,郁峻峰兄已有文详细介绍,不必笔者再饶舌了。本次出版,手稿采用原大影印,并参照手稿和通行本做了排印本附上,以便读者对照阅读。
今年12月7日是郁达夫诞辰120周年,《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的影印出版,也是对这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个性的天才作家的别有意味的纪念,书比人长寿。
2016年10月30日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