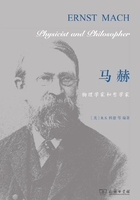
二
现在,我将转向对马赫在维也纳作为学生和年轻讲师生活的讨论,并回顾他“逆”学术地方性背景和当时科学总体情况的智识发展。马赫的物理学导师是安德烈亚斯·里特·冯·埃廷豪森和欧格斯·库必泽,前者作为与霍尔效应相关的热电效应的发现者而闻名;他作为基督教徒多普勒的继承者任物理学系主任,多普勒在位仅两年。埃廷豪森是德国大学第一位引进系统实验室练习和物理学实验训练的教授。之前,物理学通过示范实验教学,它对空间的要求不超过用来收藏由库必泽负责的实验设备的一个“柜子”。约瑟夫·斯特凡只比马赫大几岁,当马赫还是学生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轻讲师;他于1866年成为埃廷豪森的继承者。比斯特凡和马赫年长许多的约瑟夫·洛施密特开始时是一位实用化学家,只在1868年(到1891年)成为教授,后来(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讲授分子物理学。路德维希·玻尔兹曼于1861到1865年在维也纳学习,他有可能参加过马赫早期的课程。物理科学学院的杰出人物有数学家约瑟夫·佩兹伐和天文学家卡尔·冯·利特洛(小利特洛;他的父亲约瑟夫·约翰·利特洛是天文学名著《天空奇观》的作者);佩兹伐也讲授弹性体振荡,并因发明第一个消色差双目标而著名[4]。
与当时欧洲物理学的总体情况相比,维也纳物理学在19世纪50、60年代并未处于现代研究的前沿,直到80年代才通过“三驾马车”——斯特凡、洛施密特和波尔兹曼达到此位置。能量守恒定律只是逐渐缓慢地进入大学教学,与赫尔曼·冯·亥姆霍兹、鲁道夫·克劳修斯等名字相联系的热力学和分子运动论,在马赫时代的维也纳没有代表人物。在威廉·韦伯和威廉·托马森(开尔文)的电动力学领域也如是。马赫伟大的朋友约瑟夫·波普尔于1854到1857年在布拉格理工学院学习,他在回忆录[5]中写道,他在迈尔和焦耳发现能量守恒定律20年之后的1862年,第一次在另一位叫恩斯特·莱特林格的维也纳物理学讲师的演讲中听到了该定律。
因此,马赫本科阶段被维也纳生物医学领域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来自大学的生理学家恩斯特·桥和来自一家附属医学院和医院的生理学家卡尔·路德维希——的成就吸引一点也不奇怪。用现代行话说,那里就是行动之地。桥热衷于发表意见和演讲;路德维希研究生理学基本问题;他是记录生理学现象的波动曲线记录仪的发明者。他俩与亥姆霍兹、埃米尔·迪布瓦·雷蒙和鲁道夫·魏尔啸在反生命哲学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并试图将生物学整合进生物物理学,即将它整合进因果生命科学。他们在生理学研究中运用了多种物理学方法,并表明物理学应用的新的更广泛领域。马赫深受这种现代研究活动影响,他于1860到1875年间发表的以心理学和生理学问题为主题的文章表明,维也纳学派的生理学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些影响为他后来的科学哲学提供了基本素材。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另一种可能对马赫产生的影响,那就是马赫时代对哲学家、心理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教学理念的极大关注。赫尔巴特有一段时间曾在柯尼斯堡担任康德讲席,信仰康德理性哲学与实践(道德)哲学的严格分割。他的著作《作为科学的心理学》、《数学之心理学运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影响了许多科学家,也必然影响了马赫(参考文献21,第299页)。赫尔巴特后来在哥廷根任教授,他从未在维也纳任教——逝世于1841年——不过,受哲学家弗朗茨·S.埃克斯纳的影响,他的思想在奥地利广为人知。埃克斯纳从1848年起任教育部长顾问、奥地利中学或体育馆策划人,赫尔巴特教育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在这些领域得到了实现。我相信赫尔巴特教学法的总体思路在马赫身上留下了印记,特别是他(赫尔巴特)强调标的物的组织和呈现要与学习者的大脑储存过程相协调,即一种学习经济学[6]。
我以揭示马赫早期智力生活的背景为目的,追述维也纳的学术氛围。不过,他的全部哲学或世界观并不能仅仅通过对其所受学术影响的认知而变得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必须理解1848年以后奥地利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氛围,及其在教权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家庭的启蒙氛围培植了马赫的自由思想,成年后,其意气相投的朋友和合作者的观点又加强了这种自由。对马赫生命中所有这些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仍然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