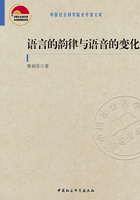
前言
自1998年退休已十又七载矣,然至今退而未休,在各级领导和学界同仁们的关怀鼓励和支持下,继续从事现代语音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应该说,这主要是跟这个学科领域的特殊性和前沿性有关:一方面,这个学科文理交叉,采用科学实验手段,以揭示人类自然言语的产生和感知机制为战略目标,因而相对比较冷门;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跟现代信息社会各方面(譬如,现代通信工程中迅速发展的计算机语音输入和输出,二语教学中的语音偏误及韵律失调的矫正,等等)对语音学的迫切需求息息相关,因而一下子又变得热门起来。作为较早涉足这个领域的探索者之一,深深感到这个学科的任重而道远。客观(虽然无形)的压力和起码的责任感令人无法停止学习新知识和探索新问题的脚步。因此,不得不放弃“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的寻常晚年生活模式,而去奋力追随这个领域的时代脉搏,勉力耕耘,希望能为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建设及其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这个人做事有点像人们形容的“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既不善于事前规划,也不善于事后的整理和总结。回顾起来,我这些年来的研究课题都是应客观需要而产生,受具体任务的推动而展开。因此,每每做完一个课题,其结果在某个学术会议上作过报告,或者所写的论文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了,往往也就抛到脑后、无暇顾及了。
然而,在频繁的学术交流或外出讲学的过程中,发现不少有兴趣的同行或学生常常向我索要那些拓荒之作(因为大都散见于不同专业学术会议的论文集里或发表在跨学科的刊物上,不易查找),或者跟我探讨其中的相关问题。这才意识到,尽管我的这些研究成果都还很粗糙,疏忽谬误之处肯定不在少数。但是,对于相关研究和应用领域的初涉者来说,也许可以从中大致窥见语音学探索过程中某个阶段、某些方面的前进足迹,了解现代语音学与言语工程学(尤其是计算机的语音合成和自动识别等智能化研究方面)结合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感受语言教学和研究对语音学知识和理论的迫切需要。同时,对于那些有兴趣做进一步探讨的人们来说,多少也能从中获得点滴启发,从而推动学术讨论和促进学科建设。有鉴于此,觉得还是有必要把散见于各处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并作了些许增删和修订,以便需要的读者查检。而于我个人,正好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听取意见、检讨不足和修正谬误的机会。
本书共收论文和研究报告35篇,主要是2004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也酌量收录少数2004年之前与本书主题相关、但尚未收录过的论文 。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汉语的韵律及一般语音学理论探索。
这部分成果主要论述汉语语音的节奏、轻重和语调等韵律结构问题。并结合汉语语调和轻重音研究,挖掘和发扬先辈著名学者的学术精髓,以推动和促进韵律研究的深化,提高韵律研究的水平。
韵律学研究在国外很早就开展了;在我国,比较系统的韵律学研究,尤其韵律结构研究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当时正值汉语的文—语合成亟须解决增进自然度的问题,需要语音学提供相关的理论和数据支持。于是,汉语韵律学及韵律结构研究就在这种科学背景下应运而生,而我就是在此情况下被迫上阵的。记得当时我还不知韵律结构为何物,只是奉命去探索语音的时域特性(timing)问题,几乎是白手起家,既缺乏中文参考资料,也很难获得外文参考资料。不得不从对汉语普通话音节的时长测量和分析开始,一步步地摸索音节内部和音节之间的时长分布规律,观察它们跟自然话语结构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了汉语节奏的基本单元和韵律的层级结构概念,并详细阐述了它们的声学语音学表现,努力为当时言语工程上的韵律切分和停、延的设置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此后,相关概念和研究思路便迅速扩展开去,客观上也对韵律学及韵律结构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同时,在此过程中发现,节奏、轻重和语调具有统一的层级结构基础和相互关联的客观语音基础。这才有了我关于节奏、轻重和语调等一系列的后续研究。首先,尝试通过对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实验分析,发掘先贤语调理论的精髓,针对汉语的特点,揭示声调跟语调并存叠加关系的内在本质。其次,结合节奏和轻重对话语语调输出的影响,阐述了语调的层次结构及其音高表现模式。力图为语音处理上的汉语语调建模和二语教学上纠正洋腔洋调提供依据和参考。
第二部分,语音学知识和理论在言语工程和语言教学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这部分成果主要论述怎样应用语音学知识和理论解决言语工程中语音处理上令人头疼的语音多变问题,以及二语教学及其科研中怎样应用语音学理论或者通过实验分析,纠正语音偏误和洋腔洋调或“Chinglish”之类的土腔土调问题。
这部分研究都是应现实的急需而做的原始的尝试,基本上都是拓荒性质的急就章,比较粗糙。同时,由于本人专业素养的局限,不少工作都是有赖于合作者的贡献才得以出炉的。借此机会,对我的合作者(恕不一一列举,具体参见论文之题注)一并表示谢诚。
第三部分,关于语音随机变化的生成机制及交际意义的理论探索。
这部分研究主要论述局部与全局两个不同层面上语音随机变化的不同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局部的语音变化发生在邻接音段之间,是由协同发音机制决定的,而全局性的语音变化发生在不同层次韵律单元边界上和韵律凸显处,主要是由话语总体的语义和语用表达需要决定的适应性调节变化;前者主要表现为音段的连接变化,后者主要表现为超音段的适应性发音增强与减缩。同时,这两种变化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彼此关联、相互制约的,那就是:局部的连接变化必须适应全局性调节的需要,而全局性的调节变化必须通过局部变化实施。这种既密切相关、又彼此制约的关系充分说明,尽管导致语音随机变化的具体动因和表现不一样,但都出于适应有效交际的需要。因此,尽管变化是随机的,表现是错综复杂的,但却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
语音的变化无处不在,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去认识和驾驭。音系学的研究注重相对宏观的规则归纳,一般语音学的研究又往往失之过于具体,缺乏全局视野。长期以来,人—机语音通讯,尤其是语音的自动识别一直为语音的复杂多变所困惑。然而,在一个语言集团内部,一个词或一句话由不同人说出来,或者由同一人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或者在不同语境下说出来,尽管其具体声学实现千变万化,然而,听话的人却总是能够感知为相同的词或话语。于是,人们相信,在语音信号中必定存在物理声学上的invariance。这个概念是Stevens于1972年在介绍量子理论时首先提出的,但始终未有理想答案。
我受此启发和推动,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路子,既从语音产生和感知的自然机制的角度,又从语音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载体的社会特性角度,论证了人们以为的“声学不变性”,实质上是对一个语言里由约定俗成的音—义联结关系决定的“不变的音系学认知”,其实就是同一语言集团的说话人跟听话人对于每一个词都拥有的、共享的语音行为规则,那就是一个语言相对不变的语音结构规则。因此,尽管具体的语音声学细节千变万化,但都是在共享的语音行为规则范围内运行。循着这个原则,就可从绝对的声学变化中找到相对关系上的不变性。也就是说,语音的变化、包括变化方向和方式都是有规律的,只要关系和条件一定(譬如由某种语义和语用表达决定的某个韵律层级边界),就可大致预测具体的语音变化(譬如那个边界前后音节的声学实现)。
第四部分,语音历史演变的现代语音学探讨。
这部分研究主要通过现代科学实验方法与传统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途径,立足于对现代方言中活的语音材料的实验分析,从自然语音产生和感知的客观机制的角度,对汉语声母与声调的古今演变关系等语言学领域长期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力图根据比较系统的实验结果,澄清一些单凭口耳听辨方法难以判断的语言实际,并进而探索汉语声母与声调古今演变的内在关系以及演变发展的动因、方向和规律。
之所以尝试采用现代实验方法研究语音的历史演变问题,主要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一方面,语音的历史变化是人类语言演变发展的一部分,研究现代语音,不可能割断历史;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实验方法无论多么先进,毕竟是种研究手段,关键是要用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解决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语料基础和基本观点出自本人对中古全浊声母在现代吴语十几个次方言中的读音所做的调查研究和实验分析。当初,由于这个领域对实验研究还不太熟悉,所以我的论文发表以后颇受质疑,甚至被视为离经叛道。然而,在国外却颇受欢迎,我在UCLA以此为基础的扩展研究论文,不但在国际知名刊物Journal of Phonetics上发表,甚至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处作为相关的教材来用,而且迅速被国际著名语音学家的著作收录(譬如:Peter Ladefoged, The Sounds of World's Languages, Language Arts & Disciplines, 1995; William J. Hardcastle, John Laver, The Handbook of Phonetic Sciences, Language Arts & Disciplines, 1999; Zhiming Bao, The Structure of Tone, Language Arts & Disciplines, 1999以及Granm Thurgood and Randy Lapolla,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History, 2003)。
本来准备回国后继续扩展这方面的探索,但因为研究室需要我研究普通话的韵律特性,因而一下子停顿了30多年。但是,随着实验研究在我国的逐渐普及,我的基本观点不但得到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可和验证,而且还常有同行戏说我的观点已经成为他们引用的“经典”。而这里列出的、30年后的这部分研究,都是应最近语言学相关专门学术会议(例如海峡两岸传统语言学研讨会、实验方言学论坛、国际吴语方言学术研讨会以及汉语方言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类型与历史层次研讨会,等等)的特别邀请而作,从颇受关注的客观反映来看,说明我的这种路子也许是比较符合客观需要的。需要说明的是,这几篇论文或报告的内容只是因审视的角度或具体的探讨目的而有所不同,而作为讨论基础的实验依据多半是一样的,因而难免有局部内容的重复,特此说明,敬请读者谅解。
2015年2月17日